■刘长允
著名作家张炜先生的新作《为孔子一辩:正儒与伪儒》,我一口气读完,意犹未尽。这部书写得何其好啊! 只有六万字左右,却拎清了有关孔子和儒学的二十多个重大问题,灼见迭出,精义纷呈。我对孔子、儒学和《论语》并不陌生,但似乎读了《为孔子一辩》之后,才真正了解了孔子的为人,才真正体味到《论语》的风采,才真正看清了儒学的实质。
《为孔子一辩》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这也是学界的共识。据有关专家统计,《论语》499段话中,有58段是专题讨论“仁”的,“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104次。关于什么是“仁”,或者说“仁”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则会有一些争论。张炜先生说,仁就是爱人,仁就是爱!“不管孔子对仁有多少解释,也总是不离‘爱人’;对人的爱惜、怜悯和同情,生存的自由,愉快、富足和幸福。为了这个目的、奔向这个结果,就是‘爱人’了。正因为‘爱人’是十分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所以面临一些眼前的事物,孔子需要不厌其烦地做出解释。”《为孔子一辩》还毫不含糊地指出“天下归仁,就是天下归爱。”《为孔子一辩》最令人赞叹和敬佩之处,是它第一次指出:“对专制王权说‘爱’和‘爱人’,这显然是最大的冒犯。”“‘爱’和‘爱人’,说到底与专制王权是水火不容的。”
经张炜先生这么一点拨,我们似乎一下子明白很多道理和事情:孔子周游列国为什么到处碰壁? 孔子与当权者的周旋为什么那么小心? 当权者对孔子和儒家为什么既敬又避而远之? 孔子和当权者的关系为什么总是若即若离? 这一切原因都在于:孔子大讲并要不断付诸实施爱和爱人,是对君主和当权者的严重冒犯,是最大的挑衅,甚至是点了人家的死穴。《为孔子一辩》中说:“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 君王野蛮残忍,民众如草莽蝼蚁。君王去世,奴隶殉葬。在这样鲜血淋漓的‘语境’中奢谈‘爱人’,会是多么刺耳。这究竟需要多大勇气,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不难想象,专制者最想剪除的,就是不停地宣扬‘仁者爱人’的人。”天天给当权者讲仁爱,就等于天天与虎谋皮,不被杀掉,实属不幸中的万幸。是什么因素使孔子不仅没有罹难,还做出了一番事业,张炜先生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君王不屑于讲仁爱,但他们也不敢公开断然拒绝仁爱,甚至有时候还会拿仁爱来作装饰;二是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和当权者是方枘圆凿,自始至终都很谨慎,“他是靠了极大的克制和生存智慧才活下来的”;;三是“大众无论多么低微多么无知,‘爱’作为一种语言,感召力和通用性还是最强的。……这种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共情力,最终保护了‘儒学’”。
提出“正儒”和“伪儒”的严重对立,厘清“正儒”和“伪儒”的界线,指出“伪儒”产生的机制及其危害,讨论如何防止“伪儒”的滋生,这是《为孔子一辩》的中心议题,也是该书的亮点所在。《为孔子一辩》的大部分章节,都是围绕着“正儒与伪儒”这一命题展开的,作者反复诉说,多方设喻,使读者对这一重大问题有了清醒的、全方位的认识。儒家分为不同派别,古已有之,战国时的韩非子就说过,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韩非子的老师荀子把儒分为七个等次,分别是:大儒、雅儒、俗儒、贱儒、随儒、瞀儒、腐儒。张炜先生根据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事实,直截了当地把儒学一分为二,“正儒与伪儒”,它们虽然是孪生兄弟,却代表事物的两极:一优一劣,一善一恶,一真一假,一利一害,一白一黑。当然了,“伪儒”并没有贴上标签,人们经常错认它为“正儒”。
《为孔子一辩》中说得痛快,“正儒之核即为爱人,那么伪儒之核就是治人”。多么分明,多么简洁。书中继续分析道:“这里的治人并非治理社会和民众的意思,而是对人的统治、辖制,是‘御民之术’。”“无论那些权势人物怎样借助无良学人,将‘儒学’说得多么繁复和条理,言之凿凿且学问深厚,都不必被迷惑,因为只需睁开眼睛就清楚了。”关于“伪儒”是如何生成和发展的,《为孔子一辩》的剖析尤见功力:“伪儒的形成,有强权者硬性强扭使用的原因,也有大儒们自己的屈从和迁就,由他们的机会主义心态所致。”张炜先生把这种“机会主义的心态”,一直追溯到至圣先师孔子那里,当然,那时的问题还不算严重。到了西汉的董仲舒,他借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问题就大了。《为孔子一辩》中这样断言:“孔子的学识无论怎样高深和正确,也只是一家之言。它一旦被王权专意尊崇,阉割和改造之路也就敞开了。获得这种地位的代价是巨大的,这就像一种商品的专卖经营,一旦某些从业者取得这种权利,他们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步骤,我们是知道的。”张炜先生对董仲舒的初衷表示出了极大的理解,“董仲舒本意并不险恶,却酿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果。他的系统言说,其中那些极为卓越的部分,也算深入堂奥,切中肯綮,细致条理。但由于他不可避免地放大了儒学的某些局部,强化了为上所用的部分,远旨近拉,便洇染了实用主义的色彩”。
对孔子性情的生动描述,对孔子一些言行的别样解读,像欣赏诗歌一样的体悟《论语》的韵味,这是《为孔子一辩》不同凡响之处。《为孔子一辩》中说:“他身上的平易与怪癖交织,怯懦与刚勇并存;有时柔善,有时凌厉。他对一些庙堂人物充满藐视,又表现出莫名的敬畏。他用地方上的土语与人交谈,一旦去了讲究的正式场合,他说起了普通话。”书中还记载了这样一桩故事:“孔子去看一位叫原壤的老友,对方坐在地上等他,两腿张开成八字。孔子说:‘你小时候不懂礼貌,长大了也没有什么见识,老而不死,真是害人的东西!’说着,用拐杖敲了一下他的小腿。”
对孔子的很多言行,几乎都可以作出多种解释。比如孔子的“述而不作”,多数人的理解停留在表面上,那就是认为孔子是讲述先王之道,自己不进行创造。张炜的解读就深刻多了,《为孔子一辩》中说:“孔子的述,既是重复过去,也是类似的光鲜借口,是为了把变革的道理讲得更清楚、更入耳入心罢了。他既然要‘述’,就一定要‘作’,因为这是无法回避的。好好总结过去,目的还是落在当下,这是古今中外所有保守主义者的基本特征。”
孔子周游列国的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为孔子一辩》以“马车驶向何方”为隐喻,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孔子颠簸流离14年,备尝艰辛,目的只有一个,为推行仁政,为了实施爱。当人们读到这些章节时,仿佛能看到那车队,听到那错杂不齐的马蹄声,感觉到孔子及其众弟子的焦虑,从而不由得敬佩和心痛。《为孔子一辩》说:“爱人而不为民众服务,爱人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将‘爱’落到实处,这是一辆辆马车奔走的目的和方向。”
张炜的小说我没有全读,但他写的《读〈诗经〉》《楚辞笔记》《陶渊明的遗产》《也说李白与杜甫》《斑斓志》《唐代五诗人》等著作,我都认真读过。张炜先生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学者和思想家。
孔子和儒学之于中国,既有学术价值,又有政治意义,既关乎历史,又关乎当下和未来。关于儒学的“现代性转化”问题,张炜说:“儒学中‘最好的东西’,与世界其他民族都是相通的、相似的。它们在言说时,表达的言辞与习惯可能是不同的,但深处含纳的原理则是一致的。也还是因为这种一致性,才决定了它的价值、它的地位,特别是它的现代属性。”是的,儒家的仁爱思想永远不会过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永远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遵奉的伦理原则。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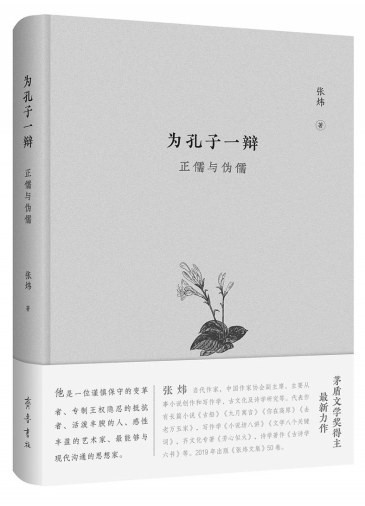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