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弛
在女性文学学科化的背景下,学者们有意识地整理出版女性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由李玲、谢玉娥主编的《新中国女性文学史料与研究》即是这一方面的重要收获。全书以详实而富有代表性的史料文献为基础,阐述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基本概念和相关问题,捕捉领域内研究范式的转换,体现女性文学自我反思和扬弃的活力,勾勒出女性文学作为“舶来品”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本土落地生根、发展流变的轨迹。
本书两位主编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发生发展的“在场者”,同时具有“选家”的眼光,既从历时性的角度客观梳理女性文学的脉络线索,又从共时性的角度准确把握它的纹理肌质。在编纂本书之前,学者谢玉娥对领域内的史料文献已有近40年的积累,对于不同代际的女性文学学者也十分了解。李玲教授则长期耕耘在研究和教学的一线,熟悉女性文学理论、参与女性文学批评实践、普及女性文学与文化。编选者的研究视域叠加起来,便覆盖了史料、理论、批评等方面。
首先,编者“在场者”的身份使得《导论》部分体现出了开阔的总体性视野。《导论》提纲挈领地论述了新中国70年的女性文学主潮,归纳了女性文学因时代变迁而形成的不同风貌,从女性主体与自我生命、男性世界、宏大历史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来评述新中国女性创作的发展脉络。其次,编者凭借“选家”的眼光甄别出那些有较强代表性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史料。这体现在文献之间具有内在的对话性、承续性,读者或能从中管窥当时学界对于女性文学相关议题的探讨和争议,或能对某一理论概念有深入、连贯的理解。随后,刘思谦于2005年在《女性文学这个概念》中进一步强调女性主体性是女性文学概念的基本内涵。李玲在《女性文学主体性论纲》中结合主体性理论、主体间性理论和叙事学等文学理论,确立女性文学内涵的女性主体性应专指隐含作者的女性主体性。多位研究者以女性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为原点,通过“接力赛”的方式深度探究了女性文学的基本原则、概念界定以及应然目的。
第二,勾勒女性文学研究的本土化轨迹。《新中国女性文学史料与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编选逻辑,即勾勒出我国女性文学研究的本土化轨迹。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表现中国本土对女性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创新吁求;捕捉女性文学研究思路的本土化转向。
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被译介到中国的高峰期。一方面,“社会性别”理论带来了全新的学术视角,使研究者感到欣喜、震撼(刘慧英:《女权/女性主义——重估现代性的基本视角》)。另一方面,研究者对这一新鲜而充满活力的理论形态进行了省思,意识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移植和借鉴其实是“借用他人的酒杯,浇自家胸中块垒”(陈志红:《他人的酒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阅读札记》);提出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这种理论要生发自批评家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和切身体验(张岩冰:《我们自己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在这一阶段内,研究者在积极“拿来”的同时也能识别出当下的“困境”——中国文本的特殊性几乎被完全消解在普遍化的西方理论视野中。时间步入21世纪,女性文学批评者开始更积极地分析困境成因,并从中寻求解决之法。如贺桂梅重新厘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所借重的理论资源,提出应将女性问题纳入更为开放的历史/现实视野之中,在主体身份多样性之间寻求适度的结合点(《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理论资源)。可见,编著表现了中国本土对女性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创新吁求。
第三,体现女性文学的自我反思和持续开放。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土女性文学因其自我反思、持续生长而具有充沛活力,在发展过程中以开放的心态警惕二元对立思维,对精英化、非理性等误区进行自觉批判。本书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新中国女性文学史料与研究》具有点面结合的编选方式、持正谨慎的编选态度,以详实、富有代表性的文献史料勾勒出本土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为新中国女性文学发展记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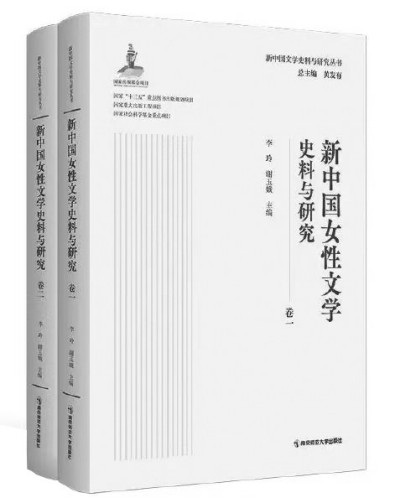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