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田
身处现代社会的人,对于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总是难免有种种隔膜——这种隔膜很大程度上并非仅仅来自于文字和文献层面,而是来自于身处异时空之下的文化心理之差异。这种差异使得我们今天在解读历史时,总是难以避免地出现种种偏移。张维玲《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所探讨的话题,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例证。
“古文运动”在今天的学术视域里,更多从属于文学研究的范围。但这一“运动”(姑且承认其为一场“运动”)究竟是在怎样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产生的? 其产生和演变之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丰富的历史脉络? 这些问题却并非仅仅在文学史的研究视域之内,就可以说清楚的。至于本书所谈论的另一个关键词——“天书时代”——对于呼吸着二十一世纪文明空气的读者来说,则更不啻为怪力乱神、荒诞不经了。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事件(historical event)之间,又是如何发生联系的? 这是本书要着力阐述的问题。
《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所讲述的“天书时代”,乃是指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终于仁宗朝刘太后去世之年(1033)的一段时间。据载,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有“天书”降于皇城承天门。真宗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的祭祀仪式,并引得朝野的响应和追捧,由此开启了所谓的“天书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骈四俪六的颂美文学成为主流,一直延续到刘太后主政的时期。“古文运动”的作家们表面上是为了批判这一文风,实质上是为了批判支撑“天书时代”的、具有谶纬神学色彩的汉唐经学。从这个角度来说,“古文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文学运动,更是一场政治文化和思想的运动。宋代士人的“疑经”思潮,也可以在这一历史脉络下,得到解释。
作者还对两场历史事件的诸多细节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推进了学界的研究。例如,宋真宗到底为什么要演出这场封祀“天书”的闹剧? 前人多认为是为了掩饰“澶渊之盟”带来的耻辱和尴尬,但作者却认为,真宗之举其实是为了实现太祖、太宗以来的“太平”的理想。这样的解读,为我们理解真宗朝的政治,提供了更为宏阔的视野。再如,在“天书时代”的展开过程中,宋真宗君臣之间发生了怎样微妙的互动? 各个士大夫群体(或派别)之间,又进行了怎样的对抗和博弈? 这些细节在本书中都得到了精彩的呈现。另外,学界关于“古文运动”,形成了“柳开—石介—欧阳修”的典范叙事,但作者指出,被石介等人极力批判的杨亿派士大夫,也在事实上促成了“古文运动”的推进。这些论点都精妙入微,可以为我们理解此期的文化文学走向,提供新视角。
读过这部著作后,我也有诸多的感触。诚如作者所述,宋真宗围绕“天书”降临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在今人看起来委实荒诞不经,但事实上却属于广义的“神文(sacred text)时代”(孙英刚语)的“正常”之举。因此,想要理解“天书时代”,需要将其放在整个“神文时代”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作者在这方面做了诸多尝试,例如在探讨宋初君臣对“太平”的追求时,追溯了汉唐以来封禅活动和“太平”观念的联结。这些论述都很好地支撑了本书的论证。但笔者读到相关论述之时,依然有意犹未尽之感。作者对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的蜕变,在很多时候受限于“儒道对立”的思维模式和惯性,认为宋真宗祭祀“天书”的活动大量融入了道教仪式,从而偏离了儒教祭礼的正轨。但事实上真是如此吗? 如果我们重新检视整个汉唐经学和政治文化的背景便会发现,恐怕杂糅了神道设教、阴阳术数的封禅仪式,才是汉唐经学的正统吧? 换句话说,在汉唐时代,儒教的祭祀仪式本身便不排斥谶纬神学的成分,这正是由其“神文时代”的特点所决定的。北宋初的“天书时代”,其实正是汉唐“神文时代”的自然延续(而非背离),并成为其绝响(或曰“回光返照”)。在这个意义上,“古文运动”的作家们对“天书时代”的批判,与其说是在伸张儒教、批判道教,不如说是儒教内部由神道设教向道德哲学的一场蜕变。不然的话,如果真宗的祭祀天书活动真的构成了对儒教的“破坏和否定”(如本书第8页所云),又如何能如此轻易地得到群臣的响应呢? 事实上,作者也多次指出,谶纬之学本身便是汉唐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被真宗君臣所接受。但是在具体论述时,限于“儒道对立”的思维框架,又时时有所犹疑,造成了论著在逻辑上的模糊和偏离。
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曾指出,现代社会从中世纪脱离的过程中,消去了传统社会的神秘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成分;“神秘”(mysteries)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了贬义词。韦伯将这一过程称为“祛魅(disenchant⁃ment)”。事实上,这样的“祛魅”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同样的表现,不过要更为曲折。我认为,中国历史的“祛魅”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唐宋之际,从“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色彩的汉唐经学,蜕变为具有人文色彩的、反神学的“新儒学”(即道学、理学或宋学),儒家经学剔除了谶纬神学、道教方术等成分,完成了从宗教神学到道德哲学的嬗变(韩愈、欧阳修等极力排斥佛老,乃至引起同时一般士大夫惊诧者,正为此也);第二次则发生在“五四”运动以后,因为受西方传来的“现代性”的影响,从传统极具道德教化色彩的政治哲学,进一步蜕变为理性主义乃至工具主义的政治学。在经历这两次“祛魅”之后,现代人对于道学主导的政治教化尚且觉得隔膜,更遑论对汉唐时代的“神道设教”感同身受了。事实上,现代学者之所以要把封祀“天书”的活动,解释为替“澶渊之盟”遮丑,也是出于一种“工具理性”的考虑,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北宋初期的时代语境。
当然,以上的商榷意见,并不能否定《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一书的重要价值和贡献。这部大著对于北宋初政治文化嬗变之精彩论述,对于学界相关研究在诸多方面的推进,相信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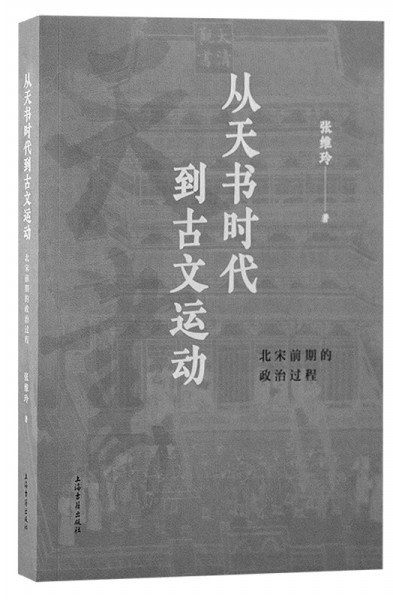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