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姣素
收到张建安的诗集《江南物语》时,才知道他不仅是个评论家,还是个诗人。评论家写诗的应不多见,有一定成果的更是凤毛麟角,美国的埃兹拉·庞德是诗人、文学评论家,他是推动意象派诗歌运动的代表人物,还有中国“九叶派”女诗人兼学者郑敏等,这些学者型诗人有一种属于他们自身的风格与特征,他们在引领诗歌潮流中起着一定的催化效应,不仅在诗体研究上有深度的开掘,还在创作中锐意探索,推动着某种文学现象或派系成熟。从张建安的诗集《江南物语》看,虽不能归类到某种派系,但字里行间、内里生发,亦有属于他的气味与质地,其在诗意江南的抒发中,有江南水乡的新韵,有叙事诗的历史感,亦有着诗性的孤独意味。
《江南物语》整体上取叙事写意,展诗性之力。全书分为五辑,从“江南意象”“江南情绪”“江南记忆”“江南怀念”“江南叙事”五个方面进行梳理归类,系统而集中地抒发了对江南的情思、情愁、情味、情感、情怀。张建安的叙事并不体现在人间烟火、日常琐碎、人物形象或是情感生发上,而是以地理坐标为背景,展现江南水乡的地域文化特征与物事变迁,在叙事的过程中偏向解说与阐释,理性而客观地抒情,点到为止,透射出历史的余辉与意味。譬如《邵阳素描》中“唐代设邵州/五代晋时曰‘敏政县’/北宋崇宁五年/分邵州西部置武冈军/南宋宝庆元年/……泛舟资江三峡/寻幽舜皇秀色……”在白描之中,追溯时空,以时间的维度漫说邵阳的历史脉络。此外写怀化、沅陵、沅水滩歌、湘黔古道等诗,韵味各异,气象有度,结合历史风物细数地域魅力与文化气息。他笔下的沅陵,在叙事抒写上又有不同的进入口吻,以历史事件呈现历史风云及其时代意味:“相传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朝廷博士官伏胜冒着生命危险/从咸阳偷运出书简千余卷/满载五车/辗转跋涉/来到沅陵/将书简藏于二酉洞中/使先秦文化得以流传后世。”诗作传情达意,叙事轻缓,循序渐进,于平实之中,呈现古人的侠肝义胆、聪明智慧、诗书情怀。这种以现实感融入历史感的糅合,让人想到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写作”。
《江南物语》从某种意义看,与“九十年代诗歌”的技艺现象有着格格不入的对比,“回到诗歌本身”之后,“第三代诗歌”出现,这些相同的诗歌范式以不同的形态体现出以现代主义为诗的最高标准。孙文波说,“一个诗人的最大愿望莫过于向世界提供一个‘文本’。”这种“文本”结合当下的诗歌创作,可理解为一种叙事形态,也就是作品内质的体现化。从“九十年代诗歌”崇尚技艺到当下的无技艺表现形式,从另一种视角去理解,标志着叙事诗的一种历史性过渡。诗歌本身的内涵是具有无限效应的,无论是情感表现力,还是精神向度,都具有蓬勃的活力与无限的张力。叙事诗虽无技艺上的“较劲”与深度提炼,实际上还是有着内在的无缝链接,在话语生发与断句之间,仍然能感知到内里的情感波动与情绪酝酿。譬如洛夫的《赠大哥》,看似云淡风轻,平淡无奇,细细思量,却能在平缓的节奏中感知到一种强烈的乡愁意味。诗人情感的波动,在舒缓有致的叙述中逐渐深沉,渐渐唤起内心的柔软与共鸣。这种内里的节奏与气韵体现出一个诗人的风格特征,张建安的《端阳》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诗人情感的闸门跟随屈原放逐江南的忧思缱绻、胸怀家国的情怀,起伏不已,悲愤交加,在时间与空间的巨大激荡之下,予人共情之力。诗人的修辞也来源于激情,这种穿越时空的联想与情绪把控,在历史感与现实感之间点燃情感的火种,掷地有声,燎原如斯。
也许,张建安的文学原乡是他出发与抵达的灵魂之地,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桃花、犬吠、篱笆、故人……日出月白,升腾着生命的颜色与光亮,氤氲着他心中的乌托邦。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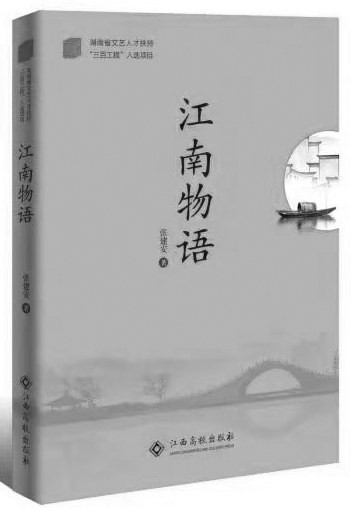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