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的人来说,巴黎是“香艳的”。“香艳的”巴黎自然让人“乐不思蜀”。1919年底赴法留国的盛成就说,法国有三美足以销魂,那便是:美景、美酒和美女。“确是令人迷的香槟酒与嫣然一笑的巴黎女儿,真是神仙,也难守戒。孟子动心之时,必曰太王好色。”诗人徐志摩说得很贴切,在他眼里,巴黎就像一床“野鸭绒的垫褥”,能把你一把硬骨头给“熏酥”了。
可是,以另一种眼光来看,还有另一个巴黎,一个文化的、艺术的、学术的巴黎。朱自清特别欣赏和留恋巴黎处处弥漫着的艺术气息,他说:“我们不妨说整个儿巴黎是一座艺术城。从前人说‘六朝’卖菜佣都有烟水气,巴黎人谁身上大概都长着一两根雅骨吧。你瞧公园里,大街上,有的是喷水,有的是雕像,博物院处处是,展览会常常开;他们几乎像呼吸空气一样呼吸着艺术气,自然而然就雅起来了。”
因此,除过一个“香艳的”巴黎外,还有一个“优雅的”巴黎。
巴黎的历史名胜、文化遗迹、建筑雕塑、绘画展览,可谓满谷满坑,实不能不看。《转角巴黎》是陈占彪教授在巴黎第十大学访学期间,在巴黎四处晃荡,寻幽探胜,搜奇访古的产物。的确,学问固然在教室里、在图书馆中、在研讨会上,但毫无疑问,学问也在生活中、在社会上、在人间。
提起巴黎,人们想到的莫过于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凯旋门等。这本书所涉及的地方,如果我们以游客的身份短期旅游的话,一般多是不会去,或者来不及去。比如总统府爱丽舍宫、桑代监狱、地下墓穴、巴黎下水道、罗亚蒙修道院、圣让·德·博雷加尔庄园、拉雪兹公墓、蒙马特公墓、蒙巴拉斯公墓、圣日耳曼昂莱城堡、圣克鲁医院、“哲人厅”、罗丹博物馆、毕加索博物馆,自然也有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等。这些地方,作者都曾经亲身踏访。
在陈占彪先生这本《转角巴黎》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中文网上能查到的内容,这里尽量不写,而中文网上语焉不详或者没有的,则尽可能详细介绍。这本书的内容多是来自相关的官方网站和法文材料,应当说既准确又权威。或许,通过这些,能让曾经看过热闹的和准备看热闹的我们,能够看出一点点门道。
比如,埃菲尔铁塔为什么被称作是“科学先贤祠”?李鸿章为什么没有登顶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的雕塑、绘画讲得都是什么意思?巴黎的“地下墓穴”里怎么藏了一个“马翁港”(Port Mahon)?物理学家安培之子让-雅克·安培有着怎样的骄人成就?将人粪视为“黄金”的雨果为何推许人粪使用的“中国经验”?1919年巴黎和会时,中国留欧学生、工人、各界代表是怎么围堵陆徵祥签约的?等等。这些问题大约都能在这本小书中找到答案。
这本书还告诉我们,晚清时期,就有一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中国外交官就曾痛快地畅游巴黎、认真地观察巴黎、仔细地记录巴黎。今天我们去巴黎旅游时,所常去的地方,他们早就去过,甚至我们所不曾去过的地方,他们亦多已到过。我们常常以为他们保守落后,其实他们脚步与世界几乎是同步的。
比如,巴黎下水道面向公众开放仅两年后的1869年7月22日(同治八年农历六月十四日),“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志刚、孙家榖,以及随员张德彝等人便曾参观游览。
巴黎公社运动刚刚平息的1871年6月9日,崇厚所率领的中国外交使团受邀来到巴黎圣母院(“那欧他达木礼拜堂”)参加法国政府为被公社处死的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Georges Darboy)举办的葬礼。
埃菲尔铁塔自1889年世博会落成后,晚清中国的一些名人要角,如1889年的张荫桓,1890年的黄遵宪,1896年的李鸿章,1902年的载振,1905年的载泽、康有为,1911年的金绍城等,曾先后登临。他们在铁塔上吃饭、远眺,充满好奇,为之惊叹。
甚至连巴黎的桑代监狱,竟然也有中国人的身影! 1910年12月6日,大理院推事金绍城等“观孙德轻罪监”。
有时候,我们往往自以为聪明,自认为开明,其实,就我们的阅历和眼界、知识和见识而论,我们一定能及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张荫桓、黎庶昌、黄遵宪、张德彝、康有为这些拖着辫子的中国官员、外交人员和知识分子? 未必。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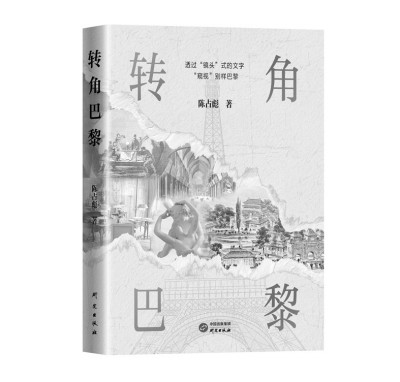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