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姣
当我们意识到生命世界的复杂性,意识到所谓科学的“真理”只是暂时正确的理论,等着新的观察和实验数据以及相应的理论来将其推翻时,现代人是否必然陷入虚无主义? 细读美国生物学家哈斯凯尔的三部曲《看不见的森林》《树木之歌》和《荒野之声》,你会发现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虚无和永恒。如果一切都是可朽的,事物还有什么实质和意义可言呢? 人类一切努力的价值何在呢?
《荒野之声:地球音乐的繁盛与寂灭》直接地凸显了这种可朽的与不朽的、刹那与永恒的对应关系:宇宙间亘古不变的寂静无声,与此间丰富多样的声音——都市的音乐会、马路的交通噪声、林间的鸟鸣虫语、山谷里动物求偶期此起彼伏的应答、海底的鲸歌等;古人类洞穴里的骨笛,与难以复原的古人类声音;农耕时代的鸟鸣与鲸语,与工业化社会人类噪声日益增多、物种栖息地破碎的环境下鸣声的变化;功能没有分化却因此获得长寿的低等生物,与经过数万年演化形成特殊属性(比如敏锐的听觉)却注定很快丧失的高级生命——演化的种种丰富成果,包括整个人类文明在内,在宇宙的运行中,或许莫过于昙花一现。
声音,形成于瞬间,消失于无痕。无论是人从嗓子里说出、由乐器传出的,还是动物凭借各种精妙的演化构造发出的,抑或自然界中天然形成的,例如风雨雷电之声,都在被人听到的一瞬飘散而去,无迹可寻。
现代科学寻求的是表象背后的本质。18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区分事物的第一性和第二性时,也只提到诸如颜色和形状等“非本质属性”,在感官经验的“梯层”中,听觉自然又要往下一个级次。正如哈斯凯尔提到的,即便在最注重感官经验的生物学实验中,也不曾有人提出要“使用你的耳朵”。“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连“眼见”的“事实”都会受到理论的“玷污”,“耳听”自然更不足为凭。
若说听觉不受重视,却也是人类最早开启的感官形式之一——在母亲子宫里,婴儿最先感受到的,是母亲身体的律动和血液流动。在幽暗的深海和地下洞穴中,声音也是生物捕食和求生所主要依赖的重要信息。声音并不原始,它历经漫长的岁月,直到有了发声器官、传播介质和接收器,才成为弥漫地球的一大奇观。我们依靠声音交流、理解彼此、躲避敌害,通过声音辨识和记录身边的鸟兽、回忆旧时熟悉的环境,也用声音表达喜怒哀乐、家国情仇。
音乐的流动感,正是缘于音符的转瞬即逝。人们从中听到时间的流逝和情感的起伏变幻。如同诗歌一样,音乐存在于真理的缝隙中,它阐述此刻的辉煌,以此照见永久。
声音来于虚空,飘逝于虚空。这种短暂促使人集中注意去聆听,也设法用多种手段去捕捉,包括录音设备,也包括无声的文字和曲谱。
捕捉刹那,将其凝固下来,无论是借助文字、录音设备还是自身的听觉和记忆,归根结底都是一个存在偏差的转录和翻译过程。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像博物学家一样,在听到“如繁星般灿烂”的一片虫声时欣然微笑,面对山谷远远传来的鹿鸣时感慨演化的神奇,在异国他乡因同一物种的叫声唤起乡愁,在远古人类的骨笛面前意识到现代人的笨拙,在繁杂的交通与物流噪声面前想到遥远地平线上的挣扎和深海难以容忍的劫难,反思人类这一物种的骄傲自大与轻狂草率。
听到,这一刹那的感官经验,足以让我们领略到人类自身的演化历程,回到我们曾经的故园,同时沉浸式地体会他者的生存体验,更好地履行我们此刻在生命共同体中的使命与责任。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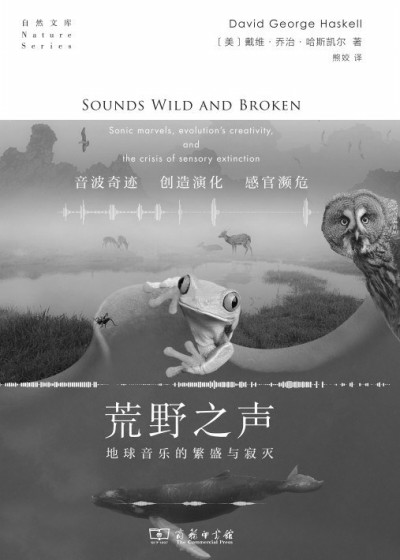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