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军事史研究往往局限于政治与社会的框架,而《战争与文明: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一书通过将历史、文学、艺术、音乐、哲学、医学、女性主义、战争法、心理学等内容纳入,构建了一个更为广泛而综合的研究框架。该书内容既包括宏观的国家叙事,也包括微观的个体叙事。作者认为在18世纪,战争与军事并非与启蒙运动相对立,而是紧密相连。“军事启蒙”的代表人物试图提倡“文明战争”,通过人道的方式进行战争,体现人类的同情心、理性和尊严。
战争与文明、军事与启蒙,似乎是截然对立的概念,但在作者笔下,这种概念上直观的对立被打破,战争和军事文化中也体现出了人性,涌现出了不少非凡的人物和作品。更值得关注的是,常见的军事史研究往往选取宏大的视角,从整体来评估军事实力、排兵布阵、胜利与失败,个体之小我往往被裹挟于时代的洪流之中。而这本书难能可贵地关注到了战争中真实的人,特别是各种弱势群体,如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外籍士兵、女性等。在这当中,对于女性的关注尤为难得,毕竟在传统的军事史中,女性几乎是遁形的。虽然女性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角,但本书对女性的着墨也相当不少,由此体现出的人文关怀是具有普遍价值的。这可能是作者皮奇切罗本人的女性身份所带来的独特视角,兹就书中关于女性与军事启蒙关系的材料及其中体现出的思想做一些评析。
第一章中对于法国军事启蒙运动中的主导力量即显赫人物的介绍中,就提及了皇室中有权势的女性探索了改善军事效能和军事教育的途径,切实推动了军事改革的进程。
第二章中重点讨论了军人的阳刚之气,而由女性主导的社交文化被认为是导致法国军队中男性“娘娘腔”风气的罪魁祸首。轻浮、肤浅、虚弱、享乐,诸如此类的负面批判凝聚为高度性别化的攻击,有人直言不讳:
世俗社交活动的准则是强调伴随着轻浮欢乐的、肤浅的社交和礼貌形式,受女性的品味、态度和行为支配。……因为轻浮、欢乐和对奢侈的嗜好被认为是女性天生的性格。(107-108页)
尽管这种对女性特质的负面表述有失偏颇,但这也体现了女性在社交文化中的强大影响力。男性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方面在这种文化中获得了一些更利于交往的特质如礼仪、优雅,另一方面也担心自己表现出饱受诟病的“娘娘腔”。
第三章的核心是战争中的同情心与人性。女性积极反对军队中施行的酷刑,如“鼓动年轻人和许多上校反对法令中规定的用军刀扁平的一面击打士兵背部的处罚措施”(210页)。
在第四章“勇士之国:人人皆可为英雄”中,“女性、战争与女性英雄主义”一节集中讲述了战争背景下的女性。
一方面,女性所具有的普遍的善良和同情心,被窄化为一种具有局限性的“小爱”,父权制社会质疑女性是否拥有普适的“大爱”,并且往往认为女性和爱国主义是没有关联的,由此女性就被排除在社会公共生活之外。这里其实存在互为因果的逻辑错误。正是由于事实上的不公,导致女性与公共事务绝缘,从而深化了这一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关于女性是否被视为“公民”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女性往往被视为与仆人、儿童同为男性附庸(所属物)的弱者。传统的厌女主义认为,女性和军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物,这与性别特质及分工有关。
作者举了贝洛瓦的《加来被围》为例。值得深思的是,这部剧作刻意塑造了所谓女性主义的角色。女性看似和男性同样拥有参与战争的机会,但官方塑造的“女性楷模”是以辅助者的角色出现的,她们只是在战争中为自己的丈夫、父亲做了一些后勤保障工作,显然这是符合传统性别分工的设定的。这是一种虚假的、形式的女性主义。在这部剧作中,所塑造的“巾帼丈夫”也从最开始的高光时刻很快隐没,转而回归到了日常的身份中,这是对女性英雄的去魅。
书中还举了圣女贞德的例子,其神圣性的根源被归结于处子之身,但却以其放荡不羁的戏剧性反转收场,似乎是故意颠覆这一圣洁的形象,不禁让人怀疑其动机可能是对于女性英雄主义的攻击和反驳。
罗佐伊的剧作《法国德修斯》中对女性的态度与此前的作品如《加来被围》形成了鲜明对比。罗佐伊颇为直接地指出:“她们品德高尚,但从来没获得过荣耀;她们人格伟大,但永远不能在战场上一展身手。”(266页)但这种正面的表彰也始终是矛盾和动摇的。
尽管罗佐伊的戏剧有许多缺陷,但它提出了一个微妙的、具有同情心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大的性别平等的形象,这种平等包括在政治、军事和英雄行为等方面的平等。罗佐伊剧本的结局是女性驱动的,它预示了20世纪女性主义批评的双重拒绝:第一,把女性角色集中安排在一起,拒绝男性的个性化模式;第二,拒绝对“母性-女性”进行还原论式的简单刻画,支持把女性看成坚强的和复杂的,她们无论在身体方面还是在心智方面都在努力斗争,以期实现平等和解放。(268页)
第五章中提及了女性公民权与参军的问题。当时法国军队中的女性比例是欧洲国家中最高的,占比高达15%。女性士兵做了很多非常先锋的尝试,提出了至今仍振聋发聩的观点,如平权。不幸的是,女性公民士兵这一身份看上去似乎是取得了进步,其实是在母职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责任。女性的地位始终是与少数族群相近的,如有色人种、外籍人员、少数民族、奴隶等,他们都在宏大的军事话语体系中缺乏一席之地。18世纪法国女性的公民身份和母亲身份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女性公民士兵体现了 自然法、公民权和传统女性角色的三位一体。列昂理想中的巾帼勇士确实是富有同情心的爱国者和“开明”的完美英雄。她同时体现了爱国、好战、情感和家庭价值观。(305页)
女性主动要求参军,再加上军队放宽条件和加大支持,以及让女性退役后重新回归传统性别观念,这一切都使女性英雄主义成为可能。(307页)
女性公民士兵被理想化为既具有传统女性美德,又具备了在公共领域展现坚韧和决心的特质,这听上去并不是什么合理的要求,因为男性士兵就不用背负这种家庭价值观的束缚,在英雄角色之外扮演额外的“家庭男性角色”;不过抛开这一点不谈,承认女性扮演英雄角色的权利本身当然是进步的,特别是当她们可以在战场上暂时抛开家庭角色的时候。这表明在军事领域中,女性无论如何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可以相对不再受到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
在传统的军事史叙事中,女性没有立足之地,一度成为软弱、情绪化与不爱国的代名词,如罗佐伊在《法国德修斯》中塑造的女性角色朱莉。女性或是作为情欲的对象——人们已经对军队中的性侵犯和性暴力习以为常;或是作为后勤人员起到十分有限的作用。美其名曰,让男人去保家卫国、保护女性,但在家国存亡的危急关头,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有保卫祖国的义务,也应该有冲上前线的权利。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以及各种征战沙场的女英雄,但她们一开始总是迫于形势、女扮男装,之后在战争中崭露头角,最后荣归故里。传统中在讲述这种故事的时候,总是侧重于弘扬或夸赞其“巾帼不让须眉”,还是以男性作为标杆,对其最初受到的歧视或不公平待遇却是一笔带过。某种意义上,古今中外的女性似乎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和不公,但可贵的是,她们总是坚韧而富有责任感,并且她们的力量正在逐渐被看见。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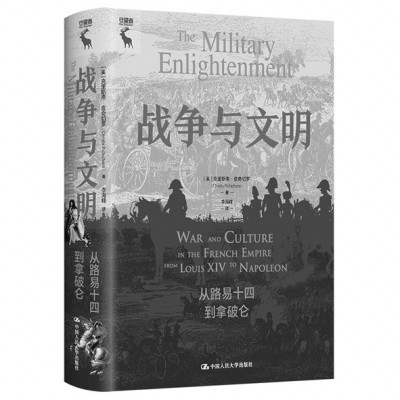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