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城市大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一段深重而屈辱的殖民历史。对这座城市20世纪初40年沉重屈辱的奴化统治做具象传达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大连作家刘东的《回家的孩子》,是一部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大连为背景,表现民族灾难年代普通百姓——尤其是少年群体抗争被殖民命运的历史题材少年小说。这一鲜见的题材与视角,令那段日渐尘封的历史得以逼真复现,也令和平年代人们日渐慵适的心境为之深深一凛。
作品落笔于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大连的至暗时刻,以药店掌柜田映川一家的生活际遇切入,关联了三代人、多个家庭,包括不同国别百姓的时代命运。作家深怀正义与悲悯,以文学之笔,揭示日本殖民者对大连人民施行的奴化教育和残酷统治,刻画出个体所历劫难、所作抗争与深具普遍意义的人性之殇。
这种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是一种典型的难度写作,需要占有大量的史料,建立在扎实的历史真实基础上,且能将史料有限的、客观的记录,做出符合历史文化语境的想象性还原,化为生动的人物与行动、场景与氛围。这既考验作家的创作准备,又考验作家的创作才情与能力。追踪过刘东的一些创作,罕有这样的题材。刘东自叙,“《回家的孩子》是我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几年来,第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而回顾这部小说的创作历程,几乎跟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年限(25年)一样长”。刘东用漫长的准备,搜集、消化了大量史料,让自己穿越般沉入历史,与那些在大连抗争命运的人们一起,重新挣扎、求生、斗争、磨砺。作品中的多个历史事件、重要情节、生活细节,都与史载记录严谨呼应。
从1905年日本占领大连至1945年日本投降,大连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下历经40年暗无天日的时光。日本人把大连视为本土之外的一块飞地,称大连为“关东州”,多种手段强推殖民教育、奴化教育。《回家的孩子》中,写到了田掌柜田映川所在的街道被改名为“上葵町”;写到了百姓生活中各种无理等级,日本人可以吃大米,中国人则无权,药店原伙计荣芳因为偷买一碗白米饭被殴打,还被判“经济罪”;公共交通有“白牌车”“红牌车”之分,仅日本人有资格乘坐干净舒适的白牌车。田映川二儿子田仲男为救病人强搭白牌车,被辱骂并被扭送派出所。尤为可怕的是,日本从孩子下手,强推奴化教育。作品写到了日本全面封杀国学、私塾,杀老师,烧校舍,手段残忍。田映川的父亲因是私塾老师,被日本特务暗杀,私塾学校被烧毁,田家被迫改行开药店。日本人强令学生进入他们开办的学校,讲授日本历史,宣扬日本文化。汉语被称为“满语”,日本语反被称为“国语”,学生被禁止使用自己国家的语言,违者重责、体罚。
正如作家所述:“一个国家的疆土、城池被侵占,还可以夺回来,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文化传承被切断,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真的彻底沦陷了,真的面临了被灭种灭族的万劫深渊。精神和文化才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最后的疆土和城池。”
《回家的孩子》为厚重的历史与沉重的主题寻找到了直击内心的文学承载。环环相扣的有效情节,严谨的故事逻辑,构成了人物立体、多维的活动场域。《回家的孩子》塑造了多个鲜活、典型的人物形象,代表着不同的立场与命运。作品高光书写了以田仲男为代表的少年英雄与以唐生为代表的中国儿童形象。
田家二子,中学生田仲男,就读于旅顺高等公学校。他机智果敢,成为自发的学生领袖,并与郑大年、向明义组成“铁三角”,带领中国学生与校方斗智斗勇。学生们被充当苦力,派去给日本人挖沟铺电缆、修军用机场,在极其恶劣的衣食条件下遭受百般虐待,甚至有学生因此身亡。田仲男带领学生们暗中破坏电缆,抵制修建军用机场,并以激怒日本学生、约群架的方式避开为日本人服役。
中日学生对决的这一夜,写得惊心动魄,写得热血沸腾。这场群架是惊动整个关东州的大事——史载“水涧堡事件”。这次暴揍日本学生,也为整个关东州百姓出了一口恶气。但代价是,三个少年因此获罪,被刑讯、毒打、利诱,向明义甚至为这次反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少年们远超他们年龄的坚强、忠义,令人泪目,更令人慨叹。
小学生唐生、田叔男,就读于松正寻常小学。弱小的孩子虽然没有能力做出像大哥哥们那样的激烈反抗,但同样以自己的方式做出抗争。烈士之子唐生,虽然年龄尚小,但是坚韧、磊落,以沉默抵抗日本教育,面对责罚从不畏缩或逃避。田叔男虽然不像唐生那样笃定,虽然也会害怕,但屡屡选择了坚持与唐生并肩。因为小飞机吊坠与日本人高则对峙那段,写到两个孩子“竟然有了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这过早承载的、远超他们心智年龄极限的恐惧,令人心酸。而无论是小学生唐生们,还是中学生田仲男们,他们身上所被寄托和承载的,正是守护家国、守护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希望。
作品取民间立场叙事,没有战争的硝烟,其主旨,是民间自发的、不屈从命运、捍卫民族尊严的“抗争”。田掌柜要求在日本学校读书的孩子们一回来先给祖宗排位鞠三个躬,要“记得自己是谁家的孩子。”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墓碑上,虽然被迫使用日本纪年或者伪满洲国纪年,但绝大多数百姓都要清楚地刻上自己的籍贯:山东、河北、河南……大连人民以各种无声的方式反抗侵略,守护着中国人的民族立场和家国信念。
当然,芸芸众生被历史的洪流裹挟,他们当中有奋争者,也有委曲求全者。作家生动展现了他们的不同选择与必然命运。“机灵”的伙计荣芳和田杜若这一条线索,以惨烈的方式呈现了另一种选择的结果。给日本人当差的荣芳,为能让怀孕的田杜若吃上一口米饭,用家传的金镏子换来日本人一碗大米饭。可日本人反手就告发了他。两个日本警察因此赶来,荣芳遭毒打并拖走,定了经济犯的罪名;杜若流产,被爹娘接回了家。荣芳机灵一辈子做得最愚蠢的事,就是想以苟且的方式求小日子平安。
同时,《回家的孩子》这部作品的意蕴层次可圈可点。作品没有终止于反抗殖民这一重主旨,也并未止步于尾声处迎来的抗日战争胜利,而是向更深处追问。尾声处,日本投降后,大连像回家的孩子一样回归祖国怀抱,获救的田仲男反而陷入一种沉重、阴郁的心境,他的内心充斥着负疚心理、复仇心理和看不清前路的迷茫。是开篇人物绍师傅再次出现,疏解、引导徒弟将个人恩怨上升到民族家国的层面权衡利害,并最终投奔为人民大众争取平等自由的共产党。在这样的民族家国危难之际,自发的、个体的反抗、复仇,往往是以卵击石或短暂胜利,抱团救国,方是真正的出路。
作品同样做出了关于道义与人性的深刻反思。日军侵华这样一种入侵,是对正义的颠覆,也是对人性的颠覆;这样一段殖民史,是被入侵者的悲剧,同样是入侵者的悲剧。那个被救的普通日本人和他的女儿田中枝子,呈现了普通日本人在殖民地令人唏嘘的境遇。他们在殖民地虽然有权坐白牌车、吃大米,但同样是艰难、孤独生存的个体,在殖民统治失败时则如丧家之犬,无人顾及生死、退路。父亲客死他乡,女儿最终被田家收养。这是平民视角的入侵者的命运,这也是那段历史中具普遍意义的日本民众命运书写。这重意蕴,让作品跳出二元对立的战争胜负思维,构成对世界和平的悲悯追问与人道反思。
作品中,有些奇妙的文字:在暗无天日、充满死亡气息的绞刑室里,“年轻的向明义感受到了一阵神奇的清风。那阵风穿墙而入,沁人心脾”,那是希望之风。结尾处,也现出一处温情之笔:入冬,回归祖国的大连迎来了第一场雪,“雪下得不急不缓,雪花也很细小,看上去轻巧而温柔,像母亲的笑容和呼吸”。在一团焦灼的历史中,这些描写如清风徐来,传递着属于“和平”的疏朗与温暖。这是《回家的孩子》文学书写的使命与力量。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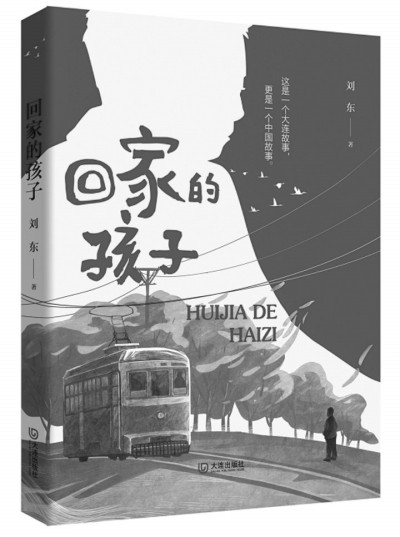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