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里,26位北大学人分享了他们在不同时代与北大的缘分和故事。韩启德先生在书的序言中说道:“大学里的传承,最重要是靠师生的纽带。”在这些打动人心的分享中,引领读者追溯北大几代学人的“学缘”,体味那波澜壮阔时代潮流下的润物耕心。
“让新生们先走,让新生们先走。”
1948年夏天,乐黛云从贵州考入北大中文系,时隔70余年的悠长回忆,让乐黛云最忘不了的还是那些为她撑起了梦想的老先生们。
大学毕业后,年轻的乐黛云决定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成了王瑶先生的学生。在她眼中,王瑶是一位“表面冷峻、内心热忱”的人,他曾经的一句话给让乐黛云记忆终身:“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就是这样一位“倔强”的老先生,一直关心鼓励着乐黛云的成长,他要求乐黛云每两周要作读书汇报,仔细为她的成果把关、仔细解释她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疑问。在王瑶先生门下,乐黛云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汤用彤先生是乐黛云的老师,也是她的公公。尽管是一家人,但汤用彤从来不会因为这一层关系而放松对乐黛云的要求,“有一次他发现我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竟然没有通读过《诗经》,感到非常惊讶。我万分惭愧,从此发愤背诵《诗经》,开会时一边做会议记录,一边在纸张边角上默写。”汤用彤先生在学术上的严格要求,和在生活中的儒雅宽厚让乐黛云用一生感念。
沈从文先生、邓广铭先生、杨晦先生、季羡林先生……一个个在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篇章的北大前辈学人,为乐黛云构筑了丰富的学术生命,更构筑了她看待世界的价值观念。
年轻的“老北大人”袁明的学生生涯因为政治运动而被一分为二。1962—1968年,她就读于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1979年她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学习,并于1982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这中间的十年,袁明在黄土高原上过着“难见一本英文书”的生活。
让袁明至今难忘的是1962年与北大西语系的第一次接触。那年的系迎新大会上,她第一次见到系主任冯至、副系主任李赋宁等老先生。看到“泰斗级大家”让袁明兴奋不已。她仍然记得,李赋宁先生在迎新会结束时慢声细语地说:“让新生们先走,让新生们先走。”“谦谦君子,实为榜样。几十年后想起那些场景,这个群体展现的是真正的人格魅力。”袁明说道。
毕业后的十年远离,袁明脑海里总是浮现在未名湖畔晨读英语、背诵诗词的画面。而老师们一次次骑着自行车到黄庄邮政局寄出来的英文资料成了袁明在西北的鞭策与慰藉。
复归燕园怀抱,攻读国际关系史的袁明很幸运地又得到了老师们的“托举”。在法律系的王铁崖先生的鼓励和栽培下,在历史学系罗荣渠先生和张广达先生的尽心帮助下,已不年轻的袁明却比读本科时更加刻苦用心。“我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从中国明清现代到英法德美意墨日,一点一点梳理。”她至今难忘张广达先生一边批改文章一边指着自己家平房院子里篱笆架的比喻:“学历史做大事年表,就像架篱笆架,先得把架子打起来,上面的花草没有架子待不住。”
生命不息,周而复始。如今,早已桃李天下的袁明在分享中这样说道:“我有幸跟随我的老师们有了一点经历,经历时代,体会人生,是幸运,更是责任。而我们还要带着历史与时代继续向前,而最大的希望还在年轻的各位。”
“先生,您别来了,我紧张呀。”
吴志攀的父亲以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得知自己儿子本科毕业要到著名法学家芮沐门下读研究生时,父亲对他说:“芮先生可是我的老师啊! 你在他面前就是一个小孩子,芮先生说什么,你听着就好了,因为你什么都不懂。”在吴志攀眼里,作为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老先生,芮沐“受过很多挫折,经过的事情太多了,很多事情芮先生都明白,只是没有说破”。
带吴志攀的时候,芮沐先生已经是74岁高龄,但依然在教学和研究上亲力亲为、尽心尽力。在吴志攀之后,先生又带了10届的博士生。直到吴志攀后来做了法律系主任,芮先生依然每次开会都坐在第一排,吴志攀曾经开玩笑对老师说:“先生,您别来了,我紧张呀。”让吴志攀记忆犹新的是自己第一次作为老师试讲,底下并没有学生,芮沐先生80多岁高龄依然坐在教室里听学生的试讲,并且给予了很有用的建议。“这对我影响很大,一个学者的认真,一个学者的远见,他对学术的负责,对国家的负责,对中国事业的负责,都是非常重要的。”
自言是1988年“蒙”上北大的孙庆伟,其导师是李伯谦教授,孙庆伟用“如沐春风”一词来形容恩师。在他身上,孙庆伟感受到了言传身教、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些词语的真正内涵。“三十多年来,李老师几乎从未对我说过重话,但他满满的期待比责备更让我感到压力;同时,李老师也从没有当面表扬过我,但他每次在身后默默的支持,又令我的前行充满动力。”
在“传承”的讲述中,孙庆伟还提到了让人感动的一件小事。2018年,孙庆伟的一本专著出版,他请李伯谦为他题写署名。“李老师一遍又一遍的换着不同的字体来写,极热的天气,写了好多种,最后让我挑一个。这就是我的老师,学生取得了一点成绩,他比自己取得成绩还要开心。”孙庆伟始终珍藏着老师每一张题写的书名,“我觉得这是老师对我最大的爱护和鼓励”。
“我在北大读书工作三十多年,遇到了很多在精神上给我以导引的老先生。我认为所谓北大的学缘就是北大的精神血脉,这是真正的北大之魂。”孙庆伟这样说道。
“一种自觉、一种活泼的平静”
程乐松是做道教研究的,最近三年他的研究兴趣是从两汉思想史入手做道教信仰和观念的研究,并且以此为视域研究中国本土信仰。尽管属于“冷门中的冷门”,但程乐松在北大总能够找到知音,身心放松地侃侃而谈。
从香港回到北京,在外攻读和工作了多年后,程乐松回到北大感受到的是北大给了他一份能够达到平衡和自洽的滋养——这在他看来是“一种自觉、一种活泼的平静”。尽管有时他会觉得这份平静也会被倏尔飘来的“夹心感”所打破:“我感觉自己被夹在两代人中间,上一代学者给你树立了榜样,你超越不了;横着看或者往下看,朋辈学者和青年学子也非常优秀,这时候可能就会慌乱。”但程乐松很快又能将自己匡扶回到平静的状态,因为他明白平静的根源是北大学术精神和传统里代代相承的宽容。“有的时候甚至是‘纵容’,我的老师就是以这么‘纵容’的方式对待我的,可能我也会把这份‘纵容’再传承下去。”
从季羡林到段晴再到叶少勇这一代,梵巴语研究在北大薪火相传。叶少勇回忆起自己刚刚开始跟随段晴学习的时候,那段艰苦的学习时光就像“打仗一样”,自己对前辈学人和段老师总是以一种“仰望”的姿态。“这时候,段老师就为我们‘祛魅’,她的口头禅总是:‘这有啥啊! 你们很快就能超过我。’”在叶少勇的眼中,段晴对学生的教导是“拔苗助长”式的,就是在这种“碾压”下,叶少勇实现了跨越式学习。推归推、严归严,让叶少勇感怀的是段晴对学生毫无偏私的托举。“有一次在段老师的帮助下,我在一捆梵文散页里发现了两部从来都没出现过的梵文材料,几乎是西藏所存的最早的经典文献,段老师特别激动,当时她就给我们系领导群发邮件,说我的学生做出了重大发现,你们应该给他嘉奖和表扬!”回忆起与恩师的种种过往,叶少勇泪中带笑:“北大梵文学科经过70年的坚守,绝学没有绝,还从后进变成了并进甚至在某些方面成了先进,我也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够为世界的梵巴语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部“传承”讲述,串起了数十位北大人的学缘求索,每一次的讲述都得益于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搭建的舞台。作为组织者和倾听者的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是邓广铭先生的女儿,父女两代都是历史学家,在她的心里,北大学人的群像是立体而生动的,北大的学缘与学脉不光属于北大,而应作为一种气质与精神,存在于历史和当下。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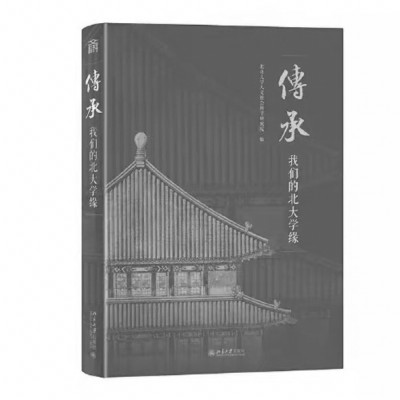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