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为
耿相新先生的诗集《复眼的世界》是典型的思想者的诗歌。这部诗集的诗学秘密,也包含在书名当中。正如诗人在作为诗集《代序》的短文《复眼,已经过时》当中所说,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是由表面上的秩序与内在的量子力学式的不确定性组成。诗人相信,世界就存在于这种秩序与无序之间。为了理解和把握这个处在巨大的和谐与悖论当中的世界,诗人曾经依赖于“复眼”般敏捷与反应快速的感性官能,但在意识到并不能由此获得关于世界更加清晰的理解之后(《跋》),遂更加依赖于思索与思考的力量。这部诗集便记录了这个转换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诗人并没有改变那种赫拉克利特式的世界观与世界认知方式,而后者似乎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诗性”世界观与“诗性”官能。所以,即便加入所谓的思索与思想,也仍然是沉潜、崛动和跋涉于肉身与具象当中的思想。
当今世界,技术在带给人们以便利和效率的同时,也使得这个世界尤其是人文价值世界面临抽象化、扁平化与碎片化的趋向。诗人是立体化的生活世界与生命意义时空的守护者,他力图重新整合与我们的肉身化生活及自由开放的灵魂相关的一个生活世界和价值时空(《分裂》)。“复眼”式的具象化与肉身化的诗路跋涉,正是对于这个生活价值时空的竭力捕捉。然而,这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这一过程的艰难,直接和直观地体现在这部诗集的文体与修辞方式上,乃至需要人们特意适应的诗句结构方式、标点符号使用方式上:在诗句当中,那些由标点符号制造的强制性的停顿与阻隔,使得作为具象的语象和意象变得突出与立体化,于是,奔赴思想的步伐在它们之间顿挫、盘曲,最终以低昂而沉郁的姿态,裹挟着语象与意象的具象性一起盘旋,凝聚与指向形而上的意味层面。这样的情形既体现在写作上,也通之于构建“灯火通明”的内在世界的阅读:
我栖息于句号之外的空白,猜想,形成
小小的旋风,宽容的翅膀,掀起
历史上的意义,迎接无家可归的,思想
(《内部性》)
标点锁定并凸显出修辞与具象性,修辞与具象连接着肉身性的生活。诗人以如此的生命基质与“意义交换”模式,从“只有自己听得懂的语言”与“自言自语”(《外在性》)的语言内部,在自问自答、自我质疑当中(《镜中的脸》),唤醒和迎来一个由诗性光亮所开启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当中,诗人信任诗性的感官权威与感性能力(《光在哪里》)。所谓的“存在”,不是抽象的共相与客观世界中的物我对立,而是“光的代名词”,诗人自己“也是光的组成部分”(《存在》):
我与我的世界,同起同灭
我的一无所知的掌上,生长出了觉悟的眼睛,它发现了不自觉的生命
(《我与我的世界》)
于是,这个“诗性”的世界万物有灵,有着其自身的逻辑和组织方式。同时,它具有以此重新组织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重新为思想奠定基础的意图(《内部性》)。但与此同时,诗人也始终是生活的具象的阐释者、思索者,和肉身幸福的崇拜者、守护者:“它像被冰冻的雪花/飘落在我灵魂的脸上,溶化/它在回忆的过程中越来越柔软/以致,用另一种语言,向我描绘前生”(《幸福》)。此种意义上的“诗性”的真理,来自于调动与协调全部官能的综合后果与思想沉积(《距离》),而非单一感官与思想抽象延展的结果。
人们永远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时间性和粒子化的河流当中流浪,似乎就是永恒的宿命:
因寻找原点我们来到了原点然而,终究,我们会像祖先一样我们将携带着原点去流浪
(《太白山》)
然而,这部诗集的真正可贵之处,是诗人在确定这种基本的不确定性的同时,没有沉溺于流变性与量子化的“诗性”世界观当中,也没有无限地放任官能、具象的权力,满足于内在世界的自足性,以及思想流浪与意义放逐式的荒凉和虚无。艾略特曾经说过,诗人的思想或者哲学理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它们的感受与表达。这样的认识有些道理,但如果推向极致则是荒唐的,因为那将意味着把(尽管是诗人的)思想或者哲学理论本身变成诗。
诗人从“相信眼睛”到“依赖思索”(《复眼,已经过时》)的转变,在诗作当中刻写下了深深的印迹,表明了诗人不懈的探索精神。经历了这种转换之后的思想,尽管没有改变其具象性和肉身化的属性,但已经有质性上的不同。诗人充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个“诗性”的内部世界,其实同样是一个辩证的、矛盾的、折叠的世界构成:“这是一个你不在场的始于未来的世界/我在我而非我的矛盾里,意念地生活”(《我与我的世界》);而生命意义的交换模型,也未必只是语言层面的(《外部性》)。
于是在这里,诗人突破内部性的顺滑与自足的“诗性”逻辑,在大开大合中把生命与精神、自然与历史、外物与主体,编织成一种富有纵深性、立体性的修辞、意象时空与语言河床(《疗饥》),在抒情短诗的有限容量与生动精致的具象万花筒当中,往往具有了民族精神史诗与文明史书写的深广格局。而在这种嶒棱的诗笔与峥嵘的现实性气象背后,是诗人作为时间之流当中的“逗号”,力图打破空乏、抽象的永恒性,构筑有限性(《断片》),进而寻找秩序性与确定性的努力:
我在非对称的时空里幻想对称,希望
你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找到你的确定
(《一种平衡》)
这种秩序与确定性,超越于“悲剧”式的绚丽的苦难与哗众取宠的苦行之上,超越于自言自语的诗性“虚构”之上。它存在于一种思想的历程当中,是一种没有“奇迹”的历险与向着“目的”性行进的艰难的自由(《上升之歌》)。
在这一过程当中,诗人完成了自我救赎,超越了在今天被以诗歌的名义加以守卫与浮夸的肤浅的自由,以及一种自以为是、贫乏任性的美学自律性。作为思想的历程,这其中也必然包含或同时就是一种更深沉、更丰厚的诗性;而在一个东方的、诗性的文化与文明传统当中,这种“思”与“诗”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更加贴切、融通与和谐的内在关联性。
总之,诗人确实不一定要创造与拥有自己的思想或哲学体系,但其原由却非艾略特式的,而是质朴的、古典的和传统的:诗歌原本就并非置身于思想与哲学外部,而诗与哲学共同面向并致力于思索和把握的那个世界,才是它们的共同基础与终极裁判。“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诗歌是以其本身的变动与丰富,来理解与呈现这个世界,并协同天地人神一起,而非仅只以其审美化的“本身”和“本体”,来彰显与见证诗性的宏阔、卓越与高贵。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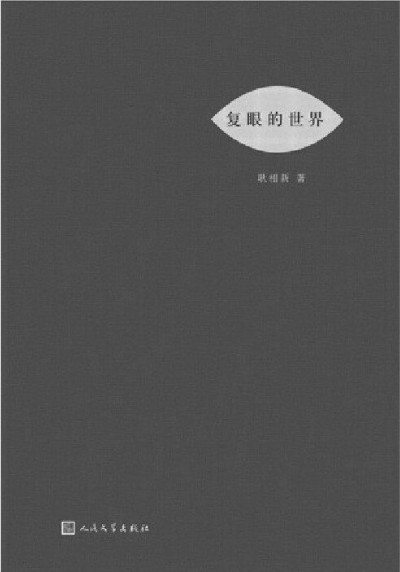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