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凯瑟的小说主题深刻、结构匀称,笔触细腻,文字优美,有抒情诗一般的悠扬韵味。
1996年,我作为交换教授去美国密歇根州的斯普林阿伯学院,在那里讲授一个学期的“中国文明与文化”课程。斯普林阿伯学院是一所有教会背景的学校,有次教会请我去社区教堂,也为当地的美国人讲讲遥远东方的中国文化,我随身带去了一把二胡。美国人对这种只有两根琴弦的“中国小提琴”十分好奇,当我演奏完一曲中国民间小调后,一位老太太起身颤巍巍地问:你能用一根弦演奏吗? 我说试试看吧。稍一思忖,我选了一小段音域较窄的曲子,即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第二乐章中那段主旋律,一曲终了,在座的老人们一个个潸然泪下,而姑娘小伙则一个个满脸茫然,不知他们的爷爷奶奶为何垂泪。
那时我刚一口气译完薇拉·凯瑟早期的四部长篇小说(《啊,拓荒者》《云雀之歌》《我的安东尼娅》《我们中的一个》),在美期间还在与三联书店的责任编辑书信往来,讨论译稿中的问题,并利用美国完备的资料完善译稿。这四部小说中有两部写的是19世纪末期美国西部移民拓荒的故事,一部是《我的安东妮亚》,另一部就是这本《啊,拓荒者》。所以我知道,那些美国老人之所以垂泪,是因为那段北美早期移民的思乡曲勾起了他们的记忆——他们从他们的父母或爷爷奶奶口中获得的记忆,记忆中当然有先辈在凯瑟笔下那片土地上哼唱这首思乡曲的情景,想必也该有这段音符曾飘荡过的那片百年沉寂、初试犁耕的土地,有野性未泯的西部旷野,有漫长空寂的大道小径,有劳瘁的耕马和疲乏的农人,有渐渐隐去的夕阳余晖,有那呼不应的永恒的苍旻;而在这苍旻之下、原野之上,曾有过他们父辈的痛苦与欢乐、追求与奉献,有过像野蔷薇般如火如荼的青春,有过不胜翘企的渴求,有过难以抑制的柔情,当然,也有过同样会令人为之落泪的收获。
《啊,拓荒 者》(O Pioneers,1913)是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第一部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是奠定她文学地位的三部长篇小说之一。小说讲述了当年中北欧移民开拓美国中西部边疆的故事,展现了移民乐观豁达的性格和坚韧不屈的精神,描写了新旧文化冲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是伯格森家的长女,他们一家是瑞典来的移民,父亲到西部拓荒十一年,刚挣扎着还清债务后却不幸中年殒命。父亲死后,亚历山德拉遵照父亲临死前的嘱托,说服了两个想卖掉土地、放弃拓荒的弟弟,栉风沐雨地经营农场,含辛茹苦地撑持家庭。眼看着日子一天好似一天,那两个弟弟却变得比当年更加自私,为了不让她那份产业将来归于外姓人名下,竟不择手段地阻挠她恋爱结婚;而小弟弟埃米尔又爱上了一位已婚少妇,结果导致了一场悲剧。亚历山德拉经受住了生活的考验,实现了父辈的愿望和追求。而她承受重负、经受考验的全部力量,都来自于她所眷恋的脚下那片土地。
小说第一部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道路开始沿分水岭地区第一条隆起地带向上延伸之时……亚历山德拉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情……也许自那片土地从地质代的汪洋中浮现出来之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怀着爱心与渴望把脸朝向它。在亚历山德拉眼里,那片土地显得美不胜收,显得富饶、雄壮而瑰丽。她如痴如醉地饱览那广袤的原野,直到她的视线被泪水模糊……每一片土地的历史都是从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心中开始书写的。”在凯瑟笔下,亚历山德拉看见的不是她眼前那片荒凉而阴沉的原野,而是一块将被人开拓耕耘的土地。那片土地有种神奇的力量,将她单纯直率的头脑和不屈不挠的意志结合成了一种对理想的忠贞。在亚历山德拉心中,这种忠贞成了一种炽热的爱,成了一种对那片土地的厚意深情,而正是这份深情和挚爱使那片土地繁荣,同时也使亚历山德拉保持了她固有的纯真。小说结尾这样写道:“幸运的土地哟,它终有一天会把像亚历山德拉那样的心灵都纳入它的怀抱,再把这些心灵融进黄澄澄的小麦、沙沙响的玉米,还有姑娘小伙们那一双双闪亮的眼睛。”这两段描写都很有超验意味。亚历山德拉是大地母亲的化身,是拓荒年代的女性形象。正是她的勇敢无畏和远见卓识给那片百年沉寂土地带来了新生,带来了文明。亚历山德拉的奋斗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移民通过艰苦奋斗实现自我的过程。
薇拉·凯瑟的小说主题深刻、结构匀称,笔触细腻,文字优美,有抒情诗一般的悠扬韵味。她从各个生活侧面描写普通人的平凡事,从人的生存问题中揭示出文化问题,把人对物质的追求融入对精神的追求。在各种现代流派风行一时之后,当今的美国评论界认为凯瑟是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斯坦福大学教授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说:“除了薇拉·凯瑟,美国文坛上还没有第二位作家以如此深切的感情、抒情诗般的恋旧情怀和坚定不移的理解,写出美国人经历中最重要的一环。”著名批评家盖斯马尔(Maxwell Geis⁃mar)则称凯瑟是“不断物质化的文明中一个精神美的捍卫者”。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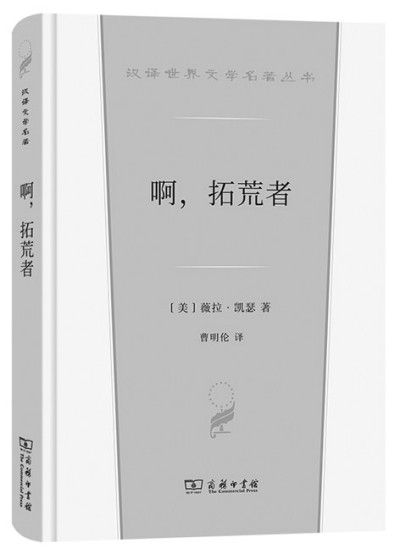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