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浪漫”这些在青春文学中被过度使用因而变得干瘪的词语,在这样的书写中再度获得了充盈的意义。
周嘉宁最新的小说集《浪的景观》收录《再见日食》《浪的景观》《明日派对》三个中篇,题材上依旧承续《基本美》中对青年生活的观察,但相较于前作,这三篇作品虽然仍以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友情关系为圆心,但有意在此基础之上辐射出一个更大的青年群落,由对个体间关系的刻画转而勾勒一种集体性的联结与创造。
三篇作品中都可以辨识出一个边界模糊但已然成形的、拥有特定文化标识的青年共同体,如《再见日食》中的国际青年写作小组、《浪的景观》中兼具地下服装批发商贩和摇滚乐爱好者身份的青年群落和《明日派对》中因音乐电台汇聚而成的兴趣社群。在时代的缝隙中,他们如同“没有形态的波段”,凭借某种微小而强韧的信号彼此识别,共同创造着属于自身的全新语言。这种创造实践使他们的青春激情在浪漫的光泽之下呈现出颇为坚实的质地,《明日派对》中两个女孩在忘我的精神热度中废寝忘食地准备节目,《浪的景观》中两个男孩风尘仆仆走南闯北的情景正是由此显得分外动人。他们付出实实在在的劳动,让本像是幻梦的理想变得确凿无比,而这种确凿又并未抹除其梦幻的光彩。“理想”“浪漫”这些在青春文学中被过度使用因而变得干瘪的词语,在这样的书写中再度获得了充盈的意义。
这三个故事无一例外均以冒险的终结和共同体的离散为结局。这固然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但是,当“庞大的物质”降落在“林间空地”,那些确凿坚实的联结和创造也忽然暴露出脆弱悬浮的“虚构”属性。在对这些青年群落的描述中,周嘉宁经常使用“虚构”这一形容。虚构,不仅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再见日食》中,四位青年初到纽约,毫无计划的他们“都极其自然地使用着从小说和电影里学到的经验”。虚构也是他们发展友情的方式:拓与马里亚诺初相识时,便都热衷于使用习自现代英语小说的书面语交谈,“竭尽可能地描述抽象的事物,有时候仅仅是着迷于词语的发音或者复杂从句的结构之美”。他们知道“现实世界里的人不这样讲话”,但“来自于小说的语言让他们变得更温和,清晰,饱含情感。于是他们乐此不疲,一点也不想去模拟现实”。虚构不只是在现实中挪用书本经验,还包括对现实经验本身的浪漫化:《明日派对》中“我”与王鹿最初通过网络聊天时,总是“忍不住把自己废物般的生活描述得更具诗意”。
更多时候,这种虚构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不如说是周嘉宁所捕捉到的青年观看世界时无意识携带的一面独特滤镜,折射着他们对自我和他人的想象性认识。这一滤镜不仅使他们对自身的经验做浪漫化的处理,也使他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表现出某种“盲视”。三篇小说都曾写到一种相似的“再认识”情境,青年主人公忽然意识到身边亲密熟悉的同伴还携带着他们从未想象过的“现实的重力”。《浪的景观》中“我”看到群青熟练地准备饭菜,才“想起来他在日本待了好多年”。事实上小说开头已经交待,群青在日本不只是“待了好多年”,而且际遇惨痛。而《明日派对》中,直到在最后的演出中见到带着孩子过来的欧老师,“我”和王鹿才意识到她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欧老师有另外一种生活”。相似的,《再见日食》中,拓在偶然通过互联网得知泉的“天才女孩”往事后“感到哀伤”,因为“他们彼此交换过那么多想法,是那么好的朋友,那些普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泉却一件都不曾和他讲过”。
拓的内心独白概括出文艺青年面对生活的一种特有的“偏见”,他们热衷于借助书本经验谈论各种抽象的事物,也能够凭借热情与天赋在擅长的领域开拓创造,却常常会忽略“那些普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偏见”正是青春的迷人甚至超越之处,使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顺着理想的浮力腾空而起,而不为其他的考量绑缚了手脚。但必然地,这种“偏见”也造成了想象与事实间的差谬,因为事实上他们每一个人都从未摆脱生活的重力,都无一例外地携带着一份历史来历和社会角色,都有着各自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周嘉宁的写作呈现出一种动人的缅怀与反思的张力:一方面,每篇小说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她对青春共同体的毫不掩饰的怀念,但另一方面,这种怀念并未滑入青春写作中常见的自恋式的沉溺,而是导向清醒的自我剖析。正因怀念是如此真挚深切,得以避免了“过来人”对青春往事的轻率贬抑,进而使得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的反思显得尤为艰难与诚恳。而更加难得的是,周嘉宁并未在天真与成熟间预设二元、单向的价值走向。她对人物天真懵懂的状态确有反省,这些小说中的青年也在经历一番曲折后“多少都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反省和悔意”,想要“对生活负起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轻易宣告了对过往的否定和对天真的超越。相反,周嘉宁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执拗,体现在文本中,她会着意强调一种改变中的不变,在沉降的反思之后再度折返回对那种天真抽象的青春精神的辩护甚至赞颂。如《再见日食》中写到,写作项目结束多年之后,拓偶然观看了一出故友马里亚诺导演的戏剧。在周嘉宁的描写中,拓的感受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他先是感到不耐烦,“剧本天真粗糙,海报上堆积着各种抽象动听的词语,导演意图暴露无遗”。但渐渐的,到了后半场,“那种令人讨厌的癫狂气息不知不觉转变成了真正的迷人。演员说的台词在拓的心里引起颂歌般的回响,海报上抽象的词语也成为类似幻觉的物质”。与此相似,在《明日派对》中,当投入极大心力的电台节目宣布商业化改版,“我”和王鹿平静地做出了离开的决定。她们既没有对自身无力抗衡庞大系统的懊丧,也没有对时代风潮和公司决定的抱怨,而是谈起了那个曾经和她们一同报名参赛的西北男孩——他在获得第一名后放弃了奖项和节目,跟随一支纪录片摄制组深入了内蒙深处的草原考察游历。“有时候我遇见困难,便想象他去的地方,想象人生的其他可能性。风是怎么样的,草又如何翻滚成浪。”这种曲折往复的摇摆辩证呈现了一种周嘉宁式的诚挚与执着。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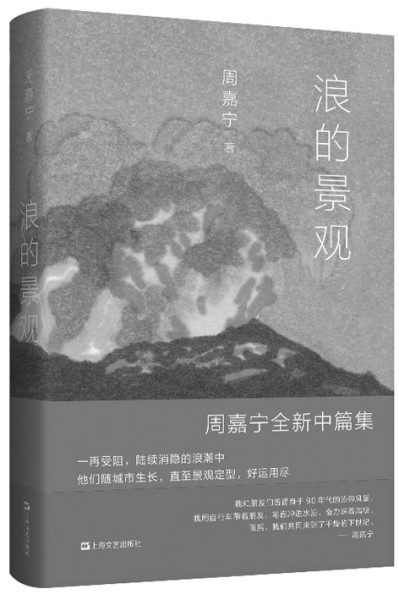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