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其实只是一个连队生活的观察者,而不是当事人。但文学的种子依然会在某个连队生根发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军人也有一代军人的文学。
“我的小说写作的确是拜连队生活所赐,没有连队就不可能有我的小说。我的连队就像一片戈壁,支撑或哺育着文学的种子在此生长。”《上尉的四季》是军旅作家王凯的最新长篇小说,以日常生活中青年军人的心理变化以及他们的人生选择,塑造了当代军旅文学的“新人”形象。
热气腾腾的集体生活让人怀念,四年的连队指导员经历是王凯此生最为重要的经历之一,那是真正意义上深入军队生活根系的四年,使他拥有了多数人不曾拥有的别样生命体验。如果说军校是他军旅生涯的启蒙,那么连队就是王凯军人生活的深造。
如今离开连队二十年了,王凯依然能清楚地回忆起那些属于连队的面孔和细节,有很多都写在了他的小说里。
中华读书报:在《上尉的四季》等作品中,显示出你对诗歌的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对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王凯:真要说起来,我读历史可能比读文学要多那么一点。历史是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的,最喜欢的史学家是司马光,我曾花了两年的时间通读《资治通鉴》,完了不过瘾,又看了一遍《通鉴纪事本末》。所以我写《上尉的四季》时,主人公马小光的名字就是从司马光那里借来的。之所以喜欢史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觉得语言特别好,一件复杂的事情能讲得脉络清晰,入传的人物几句话就描绘得栩栩如生。我在连队当指导员的时候,每天洗漱后早饭前都会背上一首古诗,然后带队去饭堂的路上在脑子里默念,不过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了。
中华读书报:《全金属青春》中汪奇写的《这夜》《九三年》等诗歌,都是你创作的吧?《上尉的四季》中也塑造了酷爱诗歌的人物形象。
王凯:可能人年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喜欢诗歌的阶段。上军校时我有个姓蒋的同学喜欢写诗,我俩住一个宿舍,他经常把他写的诗给我看,我们两个还一起订杂志,他订《星星诗刊》,我订《诗刊》,但也只是写着玩,那会儿才十七八岁,时不时会生出些莫可名状的情绪,写写诗可以抒发一下青春时的困惑和迷茫。军校里我写了大概三个本子的诗,用的是军校发的那种以校园风景作封面的蓝色笔记本,《全金属青春》里的诗都是从那上面找的。
中华读书报:《上尉的四季》共有四章,通过春夏秋冬四季展开叙述,仍然是写军营,写你熟悉的生活,是不是写起来得心应手?
王凯:写起来还比较顺手,不过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现在连队的编制、人员的结构、装备都和以前我在连队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还有就是小说中人物的变化。对写作来说,这种变化各有利弊,有利的一面是可以更理性更客观更全面地审视所要描述的生活,不利的一面是手头少了写作所需要的细节和感受。好在军队有着强大的传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军队总能不同程度地将你同化,而每个人也必须学会适应并融入军队,所以虽然我和我笔下的人物相距二十年,但很多感觉是很容易相通的,这是我所以敢去写一个当下的连队和其中年轻军人们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我再去体现年轻官兵的时代特点,他们呈现出同以往不同的样貌。在写作的时候,我用到了这两年下部队时,和战士们聊天时的一些素材和想法,还专门联系了我原来老连队的现任指导员,一位90后的年轻人,我远程向他请教了不少问题,对我写这个小说的帮助很大。
中华读书报:特别喜欢你对主人公马小光的心理描写,从最初的消极到后来的变化令人感动。
王凯:这个小说在写作过程中,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怎么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里表现一个人物的思想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又必须是自然而然的,这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小说也就立住了。在我的想象中,马小光的变化既有外力的原因,也有内心的需要,所以我就把他从山头扔到谷底,通过他从谷底向上攀爬的过程来体现他内心的变化。遇到困境然后自己努力去解决,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这里面表达的也是我对生活的一种认识,虽然写的是年轻军人的生活,但实际上关于人生困境,在任何阶段都会存在,不同的是我们面对它的态度,而马小光做了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选择。
中华读书报:你的《荒野步枪手》刚刚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这篇小说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王凯:2019年11月我去训练基地体验生活,在卡车上和战士们住了几天,真是受了一番罪,主要是草原上的冬天太冷了,我在西北戈壁滩都没那么挨过冻。当时并没有想过要写个小说,但是那几天在荒野里的日子,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所以觉得好像不写个小说有点对不起自己。一年后真开始动笔才发现并不那么好写,主要是里面少一个真正的主人公,来来回回开了好几次头,直到有一天,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年轻战士的形象,然后才感觉这个小说可以写下去了。跟以前一样,小说里面的细节都来自演习场那几天的生活,我写了当时的冷、当时的风,就连小说里面那个长长的物品清单也是完全真实的,因为那就是我去基地之前,在自己手机备忘录上列出的物品清单。可以说这个小说完全是自己被生活的陨石撞击后形成的印记,带有强烈的突然性,写作时也带着一种跟以往不同的感觉,我挺喜欢这种感觉。
中华读书报:《荒野步枪手》中写到一个人物“他写了二十年的连队生活,可现在他却不知道怎么写了。”是不是也是你的困惑?
王凯:对,我借小说中人物感慨了一下。不能不承认,连队生活是属于年轻人的,过去我曾是连队的一员,连队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连队的记忆就是我的记忆,但离开之后就永远也回不去了,我现在其实只是一个连队生活的观察者,而不是当事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文学的种子依然会在某个连队生根发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军人也有一代军人的文学。再说,每个人心目中的连队都是与众不同的,我心里那个连队还是会永远属于我的。
中华读书报:很喜欢你的语言,粗粝、生动,又不乏准确、细腻。
王凯:语言可能是小说里最美妙也最玄妙的一种存在,它和故事不同,语言本身就具有存在的价值,而无须附着于故事之上,所以我一直觉得小说的语言和小说的思想一样,是体现文学性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它的玄妙是因为这件事跟作者的个性和气质有着直接的关系,带有强烈的先天性。很多小说之所以吸引我读下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会为其中的语言着迷,但又很难说清楚究竟是语言的哪些东西让人着迷,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又是使文学独立于其他任何艺术形式存在,又不会被其他任何艺术形式所取代的基本原因。写作时我会因为某句话说得不舒服而改来改去,或者说为了找到整个小说的叙事腔调而一次次重新开始,这可能是小说写作的一种常态。我的很多朋友都说过,我小说里的人物说话跟生活中的我有些相似,这可能是因为不论说还是写,都属于我个人的某种习惯和审美。至于粗话,在我的小说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语气助词,或者是一种塑造人物的手段,考虑到军队基层生活中那严格和粗砺的一面,这其实真的跟大蒜一样正常。小说中的粗话其实也是文学的一部分,它恰好印证了文学源自生活。就像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温文尔雅,但那反倒是生活的偶然状态,我们不可能真的像开会那样生活。
中华读书报:从小在戈壁滩上的空军基地长大,军校毕业后又回到那里,直到快三十岁时才离开,这些经历给你的创作带来什么影响?
王凯:理论上讲,河西走廊并不是我的故乡,但感情上我又把那里当成是自己的故乡,这其实是父辈戍边生活带来的一种生活状态。在我心里,关于西北戈壁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我到今天还很怀念那里的晴朗、开阔和宁静。那时候出门就能看见远处的雪峰,一年有三百个蓝天,春天总是刮风,夏天最热时夜里也要盖被子睡觉,那是种田园牧歌式的回忆。但同时在很长的时间,我又很希望逃离那里,因为那里的闭塞和荒寂,似乎不能提供我想要的更好的生活。后来我真的离开了,但离开之后又会时常怀想,因为城市生活也并非我想像的那么美好,事实上我在内心里始终有些拒斥城市的喧嚣生活。这种感受我在小说里不止一次地描写过,作为一种生命体验,它始终存在并且影响着我和我的写作。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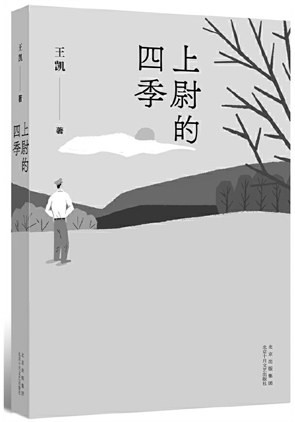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