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终究是大自然的产物,是与自然融为一体难以长久分开的天地间的灵性存在。人类的生活固然可以更好地依赖“人定胜天”以后的各种各样的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水泥建筑和繁复方便的交通设施,但是对于四季、对于农作物、对于其他动植物,对于曾经与这些自然的万事万物都和谐一致的既往生活,终于还是有一种必然的现实需要和一种可供回味与展望的沉湎需求。
对自然生活的审美回味和沉湎的表达,是相当一部分艺术家的选择。不管是诗人、画家、音乐家还是歌手,他们传达的意趣之间总是有一种这样的质地与流脉。
白庆国的散文集《乡村底色》,就是代社会传达人类情志的艺术家合唱中的一个独特声部。
在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里,万物珍贵,天人合一,俯仰四季之间,人类的生活曾经是那么艰辛而优美。大自然的细节淋漓尽致地、不吝啬、不简配地全部加于每一个人的人生,使人受限,也使人懂得自己的有限,并在有限里透彻地体会天地赐予的一切美妙。
白庆国对乡村物象饱含感情又非常精确的描写之中,始终流贯着这样一种既在生活之中又超拔于生活之外的诗情。总能从寻常的乡村物象里看到最具人文意味和美学特征的一面,比如小米、牛车、水井、石头、土墙、炊烟、村庄,蒲墩、芝麻、高粱、丝瓜、菜地、麦场等等。他的散文是将诗情融入文字的散文,很多写细碎物象的短章,已经近乎散文诗。我们能明确地倒推出来,作者之所以写了这么多细碎物象,是因为乡村环境的安静和无打扰,是因为他心无旁骛的村居状态,万事万物以本来的面貌无始无终一般地呈现在作者的眼前和心中。纯净的环境造就了纯净的观察和纯净的书写、纯净的诗。
他对每一样微小事物的书写,都是长期观察体会的结果,都是其才情的自然流露,也更是饱读诗书基础上反复训练的结晶。
白庆国写乡村是作为乡村人来写乡村。乡村生活着很多人,能写乡村的人不多。他的书写让人看到了乡村真实的一面,也看到了乡村诗意的一面。诗意源于热爱,也源于与自然融合的生活方式中更多的大自然的抚慰。
他的文字不外于乡村,而完全源于乡村本身。乡村物象和乡村人生在诗意的笔端一点点流淌,富有温暖的质地。他不回避,他捕捉到乡村人生中的善与美,不因细小而所有舍弃。
他的写作不是那种乡村出生,后来离开乡村的人的回忆。他不是外人在对乡村做观察,他既是个中人,也是因为长期阅读和写作而能将精神提升起来俯瞰乡村的本地“外人”,他在文章中多次不经意地提到他被人称为“神经病”。这个称呼的意思就是不按照一般乡下人的通常格式过普通的生活,而是有只属于他自己的精神生活方式:他是一个在乡村宅院里拥有自己的书房,凌晨三点就起来写作,经常还会在大雪大雨之中到处转悠的观察者、思想者。
文学源于生活,源于个人在真实生活中的切实感受。白庆国过着一切源于自然的生活,一直沉浸在自然的生活逻辑与环境之中,得以始终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感受与书写。
这就是下面这种说法的基础:他一直生活在乡村,这是他的劣势,但更是他的优势。
作者与所有写农村的乡土作家都不一样,他始终没有离开农村,他不是外来的观察者,也不是返乡的回味者,而是一直在乡村现场里的诗人。我相信即便不在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遮蔽自然属性的弊端的对比之下,白庆国也依然会由衷地讴歌他的村庄。他并非简单地在个人经历的对比意义上去端详自然生态下的乡间生活,而是自然而然地看到了与自然融合的生活中的艰辛与美,并且像是他笔下的那些鸟儿一样,由衷地纵情歌唱。
这是最难能可贵的。这使他的笔触之中,有只属于他自己的清新质朴真切圆融。固然这样的真切圆融必然是经历了长期反复蹉跎之后的正果,是经历了无数次表达不畅、不到位的郁闷之后,矢志不渝地笃定于自己生活场景中的这一切的描绘,逐渐才走出来,才形成现在的文字硕果的。
对于乡村物象、乡村生活的小角度叙述,其实是很要功力的。某种程度上说写一个离奇故事不难,但是写一个物品、一个场景却很难,很难写好。白庆国在这方面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写作者,他对微小物象的描绘之中,既有客观的描绘,也更有充沛感情之下的拟人、拟物、借喻、通感,因为始终围绕着物象本身,并且流贯着真情实感,所以诗化的文字不仅不造作、不夹生,还非常生动,经常带着一句话一个词就能打动人心的巧妙深邃的力道。让你感觉,只要给他时间空间,他就可以就乡间任何一个小小的物象一直讲说下去,不重复,很形象,一直调动着你随他的讲述而悲喜喟叹。
近些年有一种说法叫作诗人散文,泛意地说就是诗人写的散文,按说只要是诗人写的,不管写什么,都属于诗人散文之列无疑。不过狭义的定义可能更有意义,那就是诗人写的有诗意的散文。
也就是说诗人散文是有诗意的散文,不是知识散文,也不是说理散文,不是摆开了架势引经据典的散文。正是诗意将诗人的诗歌和散文连接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白庆国的《乡村底色》属于最标准意义上的诗人散文无疑,因为在写作这些散文之前或者同时,他已经写过上千首同样表现乡村生活、乡村物象的诗歌。这本集子里收入的散文,从篇目上看就已经与诗歌题目类似,写法也是诗歌的写法,跳过无意义的描述而直接切近最核心最独特的感受,从性质到内在气质上都洋溢着散文诗似的情致。
《乡村底色》因为流贯着与他的诗作一样的诗情而成为真正的诗人散文。那些只是因为是诗人,写过诗的人所写的散文,并不一定就直接是诗人散文,诗人散文的散文中一定要有诗情。
他行文中经常会有诗化的文字,省略前言后语的交代,直接用最凝练的词句描绘最重要的物象。
他写村庄:种地砍柴,放马牧羊,在微弱的灯光里,计划明天的事情。
他写春天:那辽阔的土地,蔚蓝的苍穹,宁静而祥和,充满慈祥的光辉。大地的摇篮里,我们能随处找到一块适合自己生长的地。
这些宏观的词句建立在那些细小事物的具体描绘之上,显得格外有根基,不是概念,而是从乡村物象之中洋溢起来的深深的豪迈。
像所有集中主题的散文集一样,《乡村底色》所收入的文章,篇与篇之间的间隔,只在叙述对象和叙述时间上有意义,在内容上其实是不存在间隔的。所有的文章都流贯着同一题材同一质地的诗意。每篇作品都是在构筑整体的乡村生活风貌的一道道具体笔触。色彩不同,深浅不一,却都有着同一的规律和韵致。
这样同一主题的散文集的普遍问题,可能是难以避免的所谓重复。不是具体的什么文章重复,是互相之间的意象上的重复,意旨上的重复。这是散文集难免的,同一题材同一形象同一作者,这么多文章传达同一种意蕴,所谓重复也就几乎是必然。好在看散文集和看小说是不一样的,散文集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大画,每一篇文章都不过是其中的一道笔迹、一抹色彩,也只有这样扎扎实实的一道道笔记一抹抹色彩叠加起来,才能形成整幅画的宏观效果。况且,散文集之不同于小说的地方还在于,随便打开任意一页,读取任意一段,无关前后线索也完全可以让人沉浸到其营造的统一意境之中去。
当然,作者也面临一个很多立足同一块土地的作家的普遍问题:仅仅是写乡村物象是不是也就最终会因为重复而流于枯竭? 当然不是物象本身的枯竭,而是创作者个人做了比较充分的表达以后的自足。每一位真正的写作者终生书写的都是他自己,而那并不直接意味着不可以有广阔的天地去驰骋。自然,这已经不是一本书的问题,而是一个写作道路与人生道路的问题了。这是写作,也是文学为创作者不断提出的吁请,其中有痛苦,也更有欢欣。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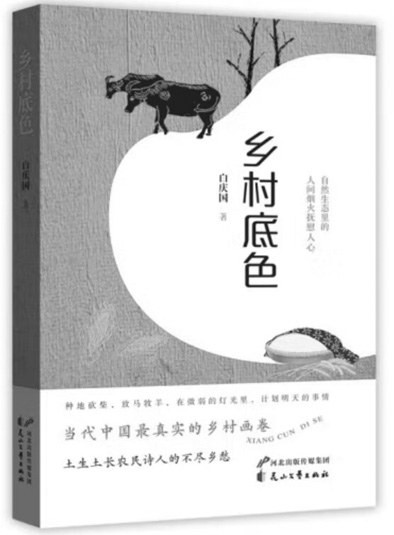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