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后,意识到欧洲并不是世界和人类的全部。于是我决定学习汉学。当时我对古代汉语很感兴趣,想知道在中国是否存在着类似西方的“智者”。语言哲学,或者说对语言的思考,在当时的欧洲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的著作是大学里辩论的主题。在哥廷根,那里的汉学家向我介绍了一篇关于孔子“正名”的文章。于是,在学习现代汉语口语的同时,我开始学习文言文。许多人认为研究中国是一项“填不饱肚子的营生”。1968年夏天,在转到慕尼黑大学继续学习汉学后,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文化和历史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领域。但我如何去中国呢? 汉堡的一位朋友给了我丽莎·尼班克(Lisa Niebank)的地址。尼班克也是汉堡人,在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做德文翻译。我们开始通信,她不断地把新的出版物寄给我。
在此期间,我读了一篇关于灵魂不死的论文,即范缜的《神灭论》。我还看了《弘明集》——梁武帝时期的一部佛教辩经文集——记载的有关佛、道、儒之间的辩论。中国的思想史和精英教育史,包括佛教在中国的作用,成为了我的研究课题。鲍吾刚(Wolfgang Bauer)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德国国家学术基金会提供的博士奖学金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使我得以在1972年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博士毕业后,我赴位于中国台湾新竹的辅仁大学语言学院继续学习汉语,之后在台北南港区的“中央研究院”工作了几个月,接着又转到了日本京都,因为中国佛教史在那里得到了特别深入的研究。傅海波(Her⁃bert Franke)拜托藤枝晃(Fujieda Akira)照顾我,后来藤枝晃又请来了牧田谛亮(MatikaTairyo)。这就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提供的理想条件。
1974年初夏,我途经韩国,并在那里参观了藏有81,340块大藏经印版的海印寺。接着,我经过中国的台湾、香港,大致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从陆路穿越泰国、缅甸、印度、阿富汗、波斯和土耳其,最后回到德国。在德国,我以自由研究者的身份生活了一段时间,将墨子的文本翻译成了德文,研究我从中国和日本带回的有关中国佛教史的资料,并最终完成了《中国佛教流派的特性和佛教通史的编纂》(1982)一书。中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这些都不断地让我着迷。但因为在德国,愿意研究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中国问题的汉学家为数不多,所以我总是面临新的挑战。例如,一个同步主义的研究小组希望我将以中文流传的摩尼教文本翻译成德文。最终,我于1987年出版了德文版的《中国摩尼教》。
陶德文(Rolf Trauzettel)推荐我在当时联邦政府所在地波恩的汉学系担任助理,使我有幸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最初频繁的政治交往。我在那里还结识了魏克德(Erwin Wickert,前联邦德国驻华大使),一直到他2008年去世之前,我们都保持着友谊。1981年,我接替傅海波担任巴伐利亚州最古老的汉学系的教师,成为了慕尼黑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自1980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我曾无数次地来到中国,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汉学这门学科的蓬勃兴起。1982年11月,我应国家出版局的邀请,在中国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在杭州,我从下榻的宾馆,可以远眺美丽的西湖。我沿着乡村的公路,来到了绍兴和宁波,一路上,到处可见池塘以及水牛拉着犁在耕作的稻田。从一个地区入手,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杭州是南宋王朝的国都,而浙江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从中世纪开始,那里就已经有了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频繁交流,其中包括日本和太平洋地区。台州、温州和宁波等沿海城市都是当时的交流中心。著名的山脉如天台山和它们的历史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我想从事区域研究,研究这一地区的过去和现在。因为对浙江省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我计划在“中国的政治、公共领域和道德——论中国公共领域的历史”这个主题框架下着手开展一项关于中国精英教育史的项目。其中的一项成果便是198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从起始到今天》(编辑注:此为德语直译),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了中文(编辑注:书名为《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文士”这个有修养的贵族形象——常常在中国的水墨画中,有时也只以竹子的形象出现——深深地吸引了我。在中国的传统中,他是“君子”,以孔子的“和而不同”为准则,但这并不意味着退让,而是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这就是中国古代“仁”的实际含义,在德语中常被翻译为“人性”(Menschlichkeit)。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挑战。但无论是今天,还是几个世纪前,我们真正需要的都是负责任的行为和正直的言论。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这种言论和文字以及相应行为的高度配合,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传统文化和人格发展的高标准被反复强调,时至今日还深深植根于受过良好教育者的意识中。值得赞赏的是,中国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并没有完全抛弃它的过去,而是以过去的基本特征为依据。强烈的乐观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色彩,它相信人有受教育的能力,只是需要一位老师,正如孔子所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接下来,我又去了中国的其他一些地方。1984年10月1日,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人之一,我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参加国庆35周年纪念活动,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我参观了兰州以及敦煌的佛教石窟,但对于浙江最大的河流——钱塘江(又名之江)的思念却从未离开过我。江边孤独的垂钓者和渔夫,一如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中国山水画中所描绘的形象,来自于对人和环境的认知传统,而这种传统很久以后才出现在欧洲,并且是在中国的影响之下。
中国的传统依然得到重视,但同时,20世纪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所思考的,始终是道德法则如何在公民心中扎根的问题,正如启蒙运动时的欧洲一样。因为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所有地方的通用法则。同时,对家的眷恋一直被看作是一种不思进取的表现。李白在他的诗歌《宴陶家亭子》中提到了石崇(249—300)的金谷园,奥地利著名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据此创作了《青春》交响曲。这种感情应该得到重视,它们需要得到关注和表达,在之江两岸和中国的所有地区都是如此。
我自己很早就和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交谈过,并且是《马克斯·韦伯作品集》编辑小组的成员。当我1993年被任命为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的馆长,将作为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和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等伟人的继任者,致力于将其发展成为欧洲文化史的研究和学习中心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没有去之江河畔,而是去了源头在哈尔茨山脉的奥克河畔。很多人对一位汉学家接替这个职位感到很惊讶,但我很快意识到,如果缺乏全球视野,就根本无法理解欧洲文化史和欧洲。年轻的汉学家和哲学家何乏笔(Fabian Heu⁃bel)说过的一句话,曾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成为欧洲人的方式就是成为中国人”。
我对中国的好感越来越强烈,我相信中国未来将继续成为欧洲特别是德国的重要伙伴国,因为我们只有在了解其他文化传统和我们自己文化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欧洲启蒙运动意义上的世界主义。为此,我们不仅要保持对话,而且要以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对待我们自己和中国的传统。长远来看,人类必须关注其未来。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的利益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并加以协调,才能取得成功。可惜的是,很多人还没有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很多事情。我们必须依靠后人,就像《愚公移山》中的老人一样。
经过半个多世纪和中国的接触,包括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我发现了诸多变化。一方面,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变得更加密切,但与此同时,政治和经济的紧张局势也日益加剧,尤为明显的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往往将人类面临的首要任务搁置一旁。但通过与中国知识分子多方面的接触,包括现在和过去几个世纪的学者、政治家和艺术家,以及当今的大学生,我愈加热爱中国的人性,正如我热爱它的诗人和思想家一般。因此,我依然满怀希望地认为,我们应当继续保护人类的人文遗产,使之成为我们共同未来的基础。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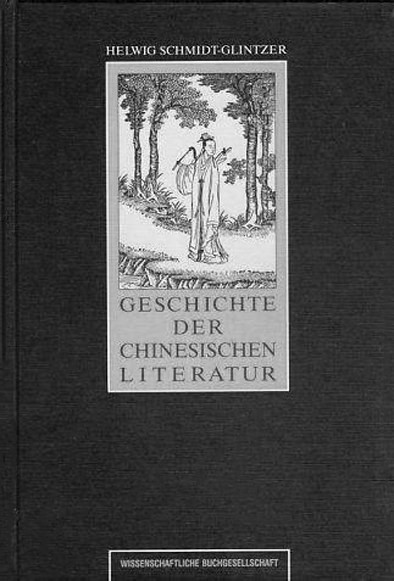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