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铮
1980年春,83岁高龄的朱光潜,不顾年迈体衰,毅然决然地开始系统翻译和研究意大利现代历史哲学家维柯的代表作《新科学》。
朱光潜惋惜自己不懂意大利文,所以只能根据英译本转译。这项翻译工作可谓艰苦,一位耄耋老人,面对这部文字古奥,内容庞杂,涉及神话、宗教、西方古代史、罗马法学、哲学、语言学等众多学术领域的五卷本巨制,而且所依据的英译本语言“又不够流利简洁”,以此他的工作强度可想而知,朱光潜坦言,在动手翻译时发现这是他一生中遇到最难译的一部书,其难度远远超过50年前翻译的三卷黑格尔《美学》。即便如此,朱光潜还是于1981年下半年初步完成了翻译工作,紧接着,他又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校对和研究工作,并附带翻译了《维柯自传》。但是他对自己的译文“深感不满”,希望有“好学深思之士细加校改或索性改译”,由此可见他对译文质量的要求是何等精益求精。1984年,《新科学》译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1986年5月正式出版。但在此前两个月朱先生已然与世长辞。
朱光潜与维柯及《新科学》的渊源与克罗齐有着直接的关系。早在20年代留学欧洲时,朱光潜就从研究克罗齐进而注意到克罗齐的精神先师维柯,及其代表作《新科学》。朱光潜曾说:“这件工作对我来说是很难的,而明知其艰难,为什么还要自不量力地做下去呢? 因为我的美学入门老师是意大利人克罗齐,而克罗齐是维柯的学生。克罗齐早已说过,美学的真正奠基人不是鲍姆嘉通,而是维柯。所以研究美学就不能不知道维柯。”60年代初,朱光潜在编写《西方美学史》时,曾用上卷的最后一章专门介绍维柯的思想体系和美学观点,对维柯的历史发展观及其“诗性智慧”对美学发展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但20年之后,朱光潜对于这次介绍很不满意,因而下定决心把维柯的《新科学》和《自传》全文转译过来。
那么,朱光潜为何要在晚年竭尽全力翻译《新科学》并重新评价维柯? 他对维柯的认识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2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观点也不尽相同。
实际上,朱光潜的晚年,在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可做的事情很多,如果只是出于愧疚,想要纠正以往在学术上的错误以弥补损失的话,那么他似乎更应该译介叔本华和尼采的作品,正如他在《悲剧心理学》中文版自序中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从1933年回国后[……]就少谈叔本华和尼采呢? 这是由于我有顾忌、胆怯,不诚实。读过拙著《西方美学史》的朋友们往往责怪我竟忘了叔本华和尼采这样两位影响深远的美学家,这种责怪是罪有应得的。”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美学是彻底的唯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格格不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译介叔本华和尼采显然是不合时宜的。85岁的朱光潜在上述这篇序言中坦陈,与克罗齐相比,他受尼采的影响更大:“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在我心灵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如此看来,如果论师承关系的话,朱光潜完全可以投入尼采门下,不必只认克罗齐和维柯;如果论“愧疚”的话,朱光潜更“对不起”的是叔本华和尼采,因为作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美学家,朱光潜不但没有译过他们的任何一部作品,也几乎没有写过几篇有分量的述评文章。
那么,朱光潜晚年译介《新科学》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想要洞悉这个问题,就应当把《新科学》与他一生思想发展的脉络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地理解朱光潜希望通过《新科学》来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成为朱光潜文艺思想,尤其是美学思想的分水岭。从此他告别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阵营靠拢,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行列,1964年《西方美学史》的诞生就是这一转变的最有分量的证据。朱光潜对维柯及其《新科学》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评述正是出现在这部《西方美学史》中,虽然朱光潜高度评价维柯“替美学带来了历史发展的观点和史与论相结合的方法”,热情赞誉他“对形象思维的研究”的论断,但最终还是严肃地指出“维柯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共同人性论”。
1983年3月,86岁的朱光潜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邀,成为该年度“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主讲人。这次香港之行是朱光潜晚年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他对此次讲座格外重视,特意将这次讲座的题目拟定为“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以下简称“影响”),似乎是希望通过对维柯看法的修正来表明自己的美学立场。
朱光潜在文中对维柯的评价与在《西方美学史》中有很多不同之处,其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变化是,他后悔自己在《西方美学史》中把维柯“看成和克罗齐一样是位唯心主义者”。《西方美学史》认为维柯的哲学思想有自相矛盾成分,既有唯物主义的一方面,也有唯心主义的一面。但在20年后的“影响”中,朱光潜却援引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拉布里奥拉和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的观点,认为“维柯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甚至在一些基本哲学观点上“维柯都是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就这样,朱光潜全面修正了《西方美学史》中关于维柯是唯心主义者的论断,从多个角度对维柯的观点和立场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化”的阐释。很明显,晚年的朱光潜是在努力“拔高”维柯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关于维柯“实践活动观点”的评价。
朱光潜晚年对维柯的评价有明显的误读成分。从维柯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的历史观并没有超出历史唯心主义的范围,因为他最终还是把人性看作是人类历史发生和发展的本源。不仅如此,他还将人类历史看作是建构人性的过程,把人性看作是衡量历史的尺度。这些观点都没有出离抽象人性论的窠臼。如此看来,《西方美学史》对维柯的评价反而更符合维柯的本来面目。然而对于朱光潜本人而言,这种将维柯过度意识形态化的误读关系到他一生美学思想的正确性和完整性的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起,朱光潜针对人性论、人道主义以及形象思维在文学艺术中的作用等问题发表的意见就不断引发美学界的争议,按他自己的话说:“这些意见和一般报章杂志中流行的议论原是唱反调”。因为在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反映论”哲学和文艺理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认为哲学思想和文艺创作都应该“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绝对不能夹带个人的思想和主观情感,否则便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其艺术必然倾向于非现实主义甚至是反现实主义——这就是典型的日丹诺夫主义的核心理论,曾经成为中国文艺思想的一种范式。在美学上一贯主张“美是主客观统一”、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朱光潜在这个范式下自然会被划入“唯心主义”的阵营。于是,朱光潜连同他介绍到中国的克罗齐一起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和围攻。时间进入80年代,中国人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重新回到美学话语场中心位置的朱光潜迎来了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这就允许他对自己以往的学术观点和发表的作品进行反思和修正,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批评进行辩驳。
纵观朱光潜一生的学术历程,尽管他晚年从未直接检讨自己对克罗齐的政治审判,但却以实际行动真诚地修复着他与克罗齐的关系,这一行动就是用生命的最后时光译介了克罗齐美学的源头——维柯的《新科学》,并以此作为自己一生学术历程成败得失的总结。作为一位将毕生精力用于研究美学的人,朱光潜在暮年对其一生的学术之路进行总结和修正是天经地义的事,只有这样才可以满足他重新建构自己美学思想体系的要求和愿望,而翻译《新科学》、介绍维柯的思想正是他为达到这一目的而精心搭建的一座理想的平台。在这座平台上,朱光潜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自己一贯坚持的美的“主观和客观统一说”造势,并以“实践论”来反对在当时哲学和文艺理论界仍然流行的“反映论”,同时再次树起“共同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旗帜。
朱光潜晚年对维柯的解读反映了他后期美学思想中一些无法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他的美学理论和观点与20世纪西方的思潮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和相同点,甚至有些论述在语言上都非常相似;另一方面,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审视美学。然而,恰恰是这种矛盾使他的美学思想愈发丰富和开放,即使到晚年也仍然跳荡着生命活力。
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建构过程始于克罗齐而止于维柯,一生与这两位意大利伟大思想家结下不解之缘,也使意大利元素成为中国当代美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18世纪后期德国的学者们重新发现维柯一样,通过朱光潜晚年对维柯的翻译和二次阐释,这位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和现代美学的奠基人穿越历史、地域与民族的界域,在中国获得了新的生命。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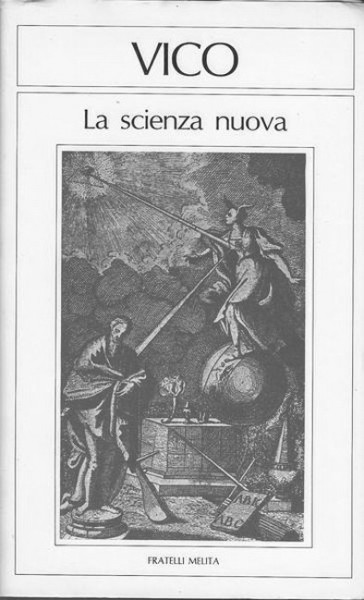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