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听说邓涛。那是有一次我的同事和朋友王原发给我邓涛诗词的链接,我打开拜读后不禁大吃一惊:这么年轻的同事,古典格律诗词写得这么多、这么好! 记忆中,我当时读后对他的五言诗尤其赞不绝口。后来,他在科学网上开博客,我默默地关注他,并经常去阅读他的博文。看得出,他是创作热情很高的人,笔勤,写得也好。后来我回所里访问时,认识了邓涛后才得知,原来他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的导师竟是我的大师姐薛祥熙先生,可见世界之小。
四十多年前,我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工作的时候,周明镇先生曾指派我帮助老所长杨锺健先生的遗孀王国桢先生整理《杨锺健回忆录》;那期间,得以阅读了大量杨老的日记和文章。记得当时给我印象至深的,是杨老的笔健。读了邓涛的新作《十年山野路漫漫》,令我看到了作者与杨老的众多相似之处。邓涛现任古脊椎所所长,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不但继承了杨老的遗志,立志把古脊椎所办成国际上首屈一指的古生物学研究机构,而且延续了杨老的文脉,每每考察一地均留下精彩诗文。
本书记载了作者自2011—2020年整整十年间野外考察的步履与行踪。虽然有些篇章以前在他的博文里读过,这次重读依然感到兴味盎然,进而爱不释手。盖因其中记载的许多人与事都是我十分熟悉的;然而,时隔多年,我又是个“懒笔头”、未曾留下过只字片语的记录,幸好读了邓涛文采飞扬的纪行,也帮助我忆起了许多有趣的经历。比如,本书开篇“天山南北”一章,其实在天山北麓石河子周边的那次考察,我与他是在一起的:我们下榻同一宾馆、考察同一剖面、参观同一农垦纪念馆。在书中的那幅丹霞地貌照片的地点,我与我的朋友张弥曼院士及瑞典同事傅睿思院士还一起留了影(见本文配图)。我那时参与张先生主持的青藏高原新生代鱼类演化与高原隆起的研究项目,邓涛作为熟悉新疆地层的专家被张先生邀请去指导我们的野外工作。除了邓涛在书中的详尽描述之外,也勾起了我对那次野外考察的星星点点的愉快回忆。
除了舞文弄墨之外,邓涛还有观鸟和摄影的爱好。野外工作是很辛苦的,他依然每天都扛上他沉重的“大炮”(全套专业摄影设备)出野外,当然他也是仰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在大家野外午餐稍事休息的时候,他就去捕捉“天高任鸟飞”的精彩镜头。他还给大家介绍那些野生鸟类的名字和习性等知识,令我们好生羡慕。本书中的多幅精彩的鸟类图片,即是他多年来在野外观鸟的部分摄影佳作。
再就是张弥曼先生与丹麦古植物学家佩德森教授那时都早已踏入了“从心所欲”之年,但在野外工作中却依然像年轻人一样不畏艰辛,勇攀高峰,令人由衷敬佩。有一次爬一个极为陡峻的山坡,脚下又是风化了的松散泥页岩,走在上面非常之滑、并十分危险。快接近峰顶的时候,由于坡陡路滑,真是举步维艰。张先生竟坚持爬上了山顶,当时大家着实吓出了一身冷汗! 在野外佩德森教授更像是小朋友闯进了糖果店一样,兴奋至极,每到一个剖面,他总是四处“乱跑”,且往往率先发现化石。由于午间天气炎热,他索性“赤膊上阵”,“撒丫子”到处寻找化石,对我们这些学术后辈来说,不啻是一种现身说法的榜样力量,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激励和鞭策。
接下来的第二章“谢家小村”,同样勾起了我对陈年旧友的追忆与怀念,尽管我从来没有机会去过那个地方。王士阶是我大学同窗、舍友以及好友,1978年初夏我从南京赶赴北京古脊椎所,参加文革后首届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当时就住在士阶的宿舍里。那时他正在准备进所后的第一次野外考察,因而十分期待、也有点兴奋。他估计我被录取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我报考的正是古哺乳动物专业,因而他也提前给我介绍了一些研究室的情况,包括他将要跟随去青海野外考察的两位研究人员李传夔与邱铸鼎。那是科学的春天,大家都鼓足了干劲。待我秋季入学进所读研究生时,他们已从野外回来。我又跟士阶与张文定成了舍友,自然听士阶讲述了许多他们野外工作的收获与见闻。因此,邓涛写的有关士阶他们一行1978年的谢家考察,我也早有所闻。也正是那次野外工作,士阶与李传夔和邱铸鼎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进所后,与李公和铸鼎兄在同一研究室,相处甚笃。掩卷思友,难免伤心,因为李公与士阶都已驾鹤而去,读了这本书,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那么鲜活。
再就是第17章“泗洪搜寻”里的下草湾化石点,我比作者早去了四十多年。我在南京大学毕业实习时,刘冠邦教授曾带领我和同窗孙卫国兄,到泗洪的下草湾化石点去考察地质并采集化石。我们师生三人还在王集公社食堂搭了好几天的伙呢!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当地还很贫困,公社食堂的伙食也很差。由于濒临淮河与洪泽湖,那里的鱼很多,有一天我们在野外归来时碰上了打鱼的村民,刘老师便买了几条鱼,准备晚上借公社食堂的锅烧出来,给我们打打牙祭、改善一下伙食。但是,在那个年代,食用油都是凭票定量供应的。无奈我们只能用白水煮了一锅鱼汤,撒点儿盐进去而已。记忆中那锅鱼汤真鲜! 我们那次只采集到了几种鱼类化石以及哺乳动物河狸的牙齿化石。不过,那是我最初采集脊椎动物化石,也算是我作为古脊椎动物学家的职业起点吧。
进所以后,我跟李公的办公室斜对门,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多有向他求教之处。李公为人谦和,没有架子;按理他是我的师长辈,然而我跟他没大没小、无谓尊长,他也跟我称兄道弟、老少爷们,无话不谈。正如邓涛在书中指出的,李公后来研究了下草湾的长臂猿化石,由于化石地点距离生产“双沟大曲”的双沟镇很近,他将其命名为“双沟醉猿”。我记得他的这种机智与幽默当年颇为研究室里的同事们所称道——翟人杰先生就在我面前啧啧称赞过李公,并让我好好向他学习。
当然,本书还有许多丰富的内容,包括了邓涛过去十年来周游亚洲、欧洲以及美洲许多国家,访问博物馆以及野外考察的记录。有些地方我去过,有些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但是读来都感到十分有趣并受益。
读罢本书,我还有另一个深刻感悟。老一辈学者多有写日记的好习惯,因而也都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不久前看到考古界前辈夏鼐先生洋洋数卷的日记出版发行,更感受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在我成长的年代,由于目睹了太多的人因为写下的文字(包括私密的个人日记和笔记)而招惹了很多麻烦,甚至于付出了惨重的人生代价,所以我从来不写日记,生怕一不小心留下文字证据(paper trail),祸从“笔”出而引火烧身。结果,尽管我年轻时自觉有过目不忘的本事,现在发现对于多年前发生事情的一些细节,单凭记忆还是靠不住的。因此,看到邓涛在繁忙的科研与行政工作中,坚持不懈地写下了这么多文字,真的令我十分钦佩。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况且邓涛还有个令人羡艳的好笔头,他的一系列随笔文集(包括本书)的出版,便是明证——我毫不保留地将它们推荐给所有的读者朋友。
我跟邓涛隔着一片大洋,相处时间并不多。我们之间虽算不上深交,却也“文字缘同骨肉深”。最后,我不揣露丑,借用他本书前言结尾所引的《一剪梅,藏北科考十周年》韵,戏做“打油一剪梅”来结束这篇短文:“十年山野路漫漫,登过山巅,宿过营边。笔耕不辍未曾闲,风情画面,字里行间。吾所文脉长连绵,代有王建,不乏张先。能文能理能宣传,耍得骨片,吟得诗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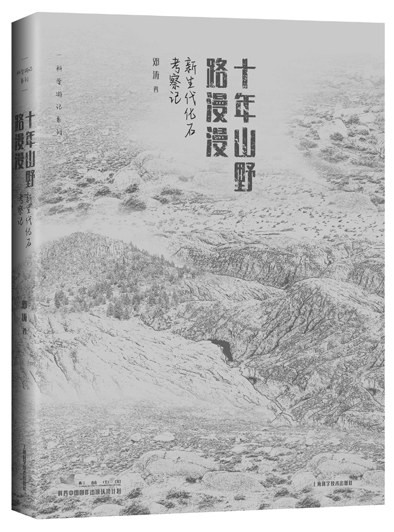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