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打开地图的话,不难发现,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大型城市——世界的知识、文化和权力的中心——都有河流从中穿过。就拿中国来说,北京有永定河,上海有黄浦江,广州有珠江,甚至高居雪域之上的拉萨也有拉萨河……美国布朗大学地球、环境和行星科学教授劳伦斯·C·史密斯《河流是部文明史》一书就深刻揭示了河流与文明(城市)深刻的关联性。
就像书名显示的那样,史密斯实际讨论的是“河流”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自然是离不开水的,定居社会姑且不论,哪怕是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是“逐水草而居”,比如一统草原的成吉思汗,他的起家之处也是“斡难河源”。并非巧合的是,旧大陆上的“四大文明古国”正与当地的伟大河流密不可分。古埃及文明被称为“尼罗河的赠礼”当然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同样也是古代文明的摇篮。在史密斯看来,“文明都是沿着宽阔、平坦的河谷兴起的,这些地区拥有肥沃的沉积土壤,但鲜有雨水的浸润。在这些地区,很难发展出以雨水灌溉为主的农业,因而河水灌溉就成了这些社会发展和生存的重要条件”。“农业的成功地发展实现了粮食盈余——尤其是可以储存的谷物。而围绕着盈余的粮食展开的征税、贸易,又衍生出了新的职业、社会阶级和城市”,最终跨过了文明的门槛。
除了农业之外,河流还有工商业的价值。就像许多西方学者一样,史密斯在《河流是部文明史》里也举出了自己熟悉的中世纪西欧经济发展中的例子:在11世纪至12世纪,安特卫普、根特和鹿特丹等西欧城市沿着莱茵河-默兹河-斯海尔德河三角洲上的通航河道蓬勃兴起,船运和商贸已然成为城市发展的原动力,意味着旧时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领主制和农奴制终将崩溃。
二
《河流是部文明史》还讲到了人类对于河流的争夺:长期以来,河流一直在默默参战。在二战中,它们天然生成的水力资源,曾为加拿大的铝业生产助过一臂之力,也使得德国的鲁尔山谷成为英国空军惩戒纳粹的地点。河流作为疆域边界和防御壁垒,自然是敌国意欲夺取的目标,有时候会引发重要的历史转折,例如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华盛顿穿越特拉华河……都足以彰显河流作为军事通道的重要价值。至于《河流是部文明史》提到河流本身“很少(如果有的话)引发战争”似乎并不太严谨。因为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的直接起因,就是两国对阿拉伯河(为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卡伦河汇流而成)的主权争议:伊朗要求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而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宣称对全部阿拉伯河拥有主权。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河流的争夺实即对河水的争夺。史密斯在书中提到,“如果自然地理条件允许上游国家在境内引流河水,或是阻截河流,将会对下游国家产生极大的威胁”。这样的情况的确比比皆是:在非洲,安哥拉则控制着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赞比亚、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重要的水源供给。在亚洲,尼泊尔控制着印度的一大水源,而印度则控制着(更下游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供水来源。
但最典型的例子,还是非洲的尼罗河。尼罗河有两大源头,发源于东非大裂谷的白尼罗河与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青尼罗河,其中,59%的水来自于青尼罗河。换句话说,埃塞俄比亚控制着苏丹和埃及的一大水源。长期以来,尽管埃及位于尼罗河最下游,但它一直都是消耗尼罗河河水最多的国家。到了现代,尼罗河流经1000英里,穿越了贫瘠的撒哈拉沙漠,最终被阿斯旺大坝所拦截,形成了庞大的人工湖纳赛尔水库。从1970年起,纳赛尔水库终结了埃及每年定期出现的洪水泛滥,为埃及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了稳定的水源和电力。这种情况随着埃塞俄比亚在青尼罗河修筑“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发生了改变。这座宏伟的大坝有155米高,1780米宽,是非洲最大的大坝。它拦截的水量能填充1870立方千米的水库,与纳赛尔水库相近。这一水利系统所能产生的电力高达6000兆瓦,约为阿斯旺大坝产电量的3倍。但对埃及来说,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的储水量非常大,可以在几年间吸走青尼罗河的流水,青尼罗河要是突然不再流淌了,埃及的生存和发展就危在旦夕了。好在,现实里的发展比《河流是部文明史》(原书出版于2019年)的预料乐观一些,2020年7月15日开始蓄水,2022年2月20日,复兴大坝已投入发电。下游的埃及并未遭受灭顶之灾。
三
实际上,大坝本身就是个颇具象征性的事物。它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力量的象征:河流孕育出的人类文明,已经能够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反过来改造河流。但这并非毫无代价的——尤其是在生态上。《河流是部文明史》举了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卡梅尔河的例子。1921年,当地建起了106英尺高的圣克利门蒂大坝。它为“沙丁鱼罐头厂,乃至蒙特雷逐渐增长的人口,提供了重要的水源”。但对一种洄游鱼类硬头鳟来说,这却是灭顶之灾。因为大坝的存在,硬头鳟再也无法进入卡梅尔河的上游产卵了。大坝建成之前,每年约有20000条成年硬头鳟在卡梅尔河里簇拥洄游,十分壮观,但在新大坝建成后,这一数字逐渐减少。2015年,在圣克利门蒂大坝下存活下来的硬头鳟仅剩7条。也正是在这一年,圣克利门蒂大坝被拆,硬头鳟终于重获生机。耐人寻味的是,大坝的拆除并不是为了拯救这个物种,而是出于经济原因。一方面,建筑物年久失修,使得很多20世纪早期的河流工程已丧失了功用。另一方面,快速增长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能力,降低了可再生电力的价格,则削弱了水电大坝的经济收益。
当然,河流大坝带来的环境危害,的确增强了移除大坝的呼声。但就像《河流是部文明史》承认的那样,“这些呼声只存在于一小部分富裕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在2019年就拆除了近1600座大坝,而美国目前约有8000座大坝(包括小型工程)。但与此同时,“世界上的发展中经济体,还在建造或计划建造上千座新的大坝”。作为一位从事地球环境研究的学者,史密斯的立场显然是反对修建大坝的。在他看来,在河上修建大坝能获得许多短期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但伴随收益而来的是长期的代价——比如,水利工程老化、水库被沉积物塞满以及渔业衰败。
不过,与其说这体现了史密斯的专业素养,倒不如说是反映了某种思维局限。要让埃塞俄比亚这样仍在与饥荒、贫困、电力匮乏做斗争的国家,将河流环境放在第一位,显然是不切实际,甚至不道德的。“每年,我们都得向国际社会讨要食物……是很丢脸的”,成千上万的埃塞俄比亚人不惜跨越数百英里,来到该国人口稀少的偏远边境,一窥复兴大坝修建工地的情形,这正是因为这座大坝承载了埃塞俄比亚“复兴”的希望。
而这一点,恰恰又与《河流是部文明史》的主旨不谋而合:人类社会依靠河流获取自然资本、交通渠道、领土疆域、健康躯体和权力,因而得以繁衍千年。可以说,如何对待河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永恒主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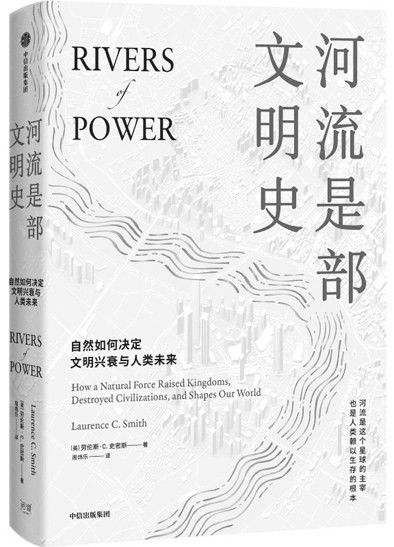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