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草:中国植物人文小史》爬梳文献,考镜源流,给中国草木写传。《诗经·摽有梅》中的梅是梅子树,而非梅花树;《九歌》“桂酒椒浆”,桂酒非桂花酒,椒浆也非辣椒水。作者以人文观照草木,书写也就草中见人,木上见文,将草木置于人之文化史中,遂有草木人文。
说是草木人文小史,但这背后的文化世界是广阔而浩大的。单看作者列出的参考书目,从诗骚名物、本草书、农书、园艺书、字书,到笔记杂著、民俗岁时、地方志……就能想象一个现代学人如何大海捞针般于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寻找一草一木的历史遗迹。沉在故纸堆的深渊里,只为搞清楚古人眼里的枸杞之“枸”之“杞”为何物,“采芳洲兮杜若”的杜若又是怎样一棵香草……在古老的典籍里,我们看到古人世界里的草和树,也看到古人面对世界的想象和思考,情感与趣味。
撰写自己民族的植物史,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说,无疑是一场精神的壮游。尽管有时只是毫不起眼的野草野树,但就像爱德华·威尔逊所说:“只要我们愿意把视界从眼前垂直下移一臂之遥,一辈子人生都可以投注在围绕一株树干的麦哲伦之旅上。”《文心雕草》的草木史之旅不止于一片叶子到另一片叶子的距离,更是心灵地域的扩张和探索。
作者的草木之旅在历史之河里,但并未因此而失去对生命的体贴。白色槐花曾是作者作为北方孩子的美食与欢乐,而初到江南,雪天盛开的红色茶花给他震撼。这些草木之文中,“我”总是在场。从深夜写到凌晨,从上古写到现代,从屈原的“芳洲”写到鲁迅的“百草园”,读者也就跟着作者一同经历柳暗花明的精神历程,一同感受到心灵史与文化史中精微与宏大的场景。童年读过的故事,少年读过的诗,北方乡村的木槿花炒鸡蛋……
虽然在传统文化史里寻觅草木变迁的历史遗迹,但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出身,也让他时时想起民国那些人与事。在青藏高原遇见骆驼刺,会想起《本草纲目》所记的边疆旧俗,更想起《骆驼草》这本杂志,以及一群专心致志做书生的文化人;写木槿花,古代辽远的事要说,但也忘不了鲁迅《朝花夕拾》里的那些朝开暮落的花……
泡桐,他从《书经》的“峄阳孤桐”写起,他热爱古籍古歌里的树,也念念不忘自己和一棵树的遭遇。深夜的街头遇见泡桐花,他写:“暗夜里,满眼白色花,像是浮雕在夜的黑石之上。而花,如清澈的星空,铺天盖地……”丰富而细腻的感受力,让名物考证的草木之文也有了热情和诗意。文字是舒缓、诗意的,自有一种典雅的气质。整本书找不到一句网络和市井流行语,这种对文字的坚守,对汉语质地的要求,也是对心灵质地的捍卫。
不管是钦定的《广群芳谱》,还是民间权威的李时珍,他都要继续探索与考辨,在学术面前,钦定与权威皆非金科玉律。一个不复制的心灵是有自己的殊异性的,一种真知灼见的背后,都是心灵与头脑纠缠和思辨的结果:采薇采的是什么? 卷耳到底是什么菜? ……考辨这些生长在古籍里的旧物,是一个现代读书人对一种古老传统——名物考证的延续,但也更是一种情感——一种对文化和天地万物的情意:每一种草木的背后,都有着古人的生活与心灵,他热爱那些生活与心灵。
“余生无所好,唯嗜花与书”,清人陈淏子在《花镜》序言里的这句话,作者常常提及,这也是他热爱的生活。他在露台上养花栽草,每天去看它们,和读书一样是他的日常。他热爱鲁迅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他也用草木和草木之文建构着自己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
沉浸草木人文,并非躲进草木丛中象牙塔里做隐士,做悠闲有趣的草木之文,他有明确的身份定位——读书人。执拗的读书人是书呆子,书呆子总是有话要讲。从“文与心”到“学与文”两辑,我们都能看到一个书呆子在历史之光的烛照下,对当代中国生活的思考。入之以草和木,出之以文化与思想,细腻的感觉、体验,加上理性的思辨,构成了他参与世界的方式,简单而纯粹。
对自然草木的感受和诗性描绘,对文化的求索与回归,共同构成了这本《文心雕草》。草木世界与历史文化都浩渺如宇宙,一本书无法穷尽,但它至少给读者呈现了一种新的认识视角……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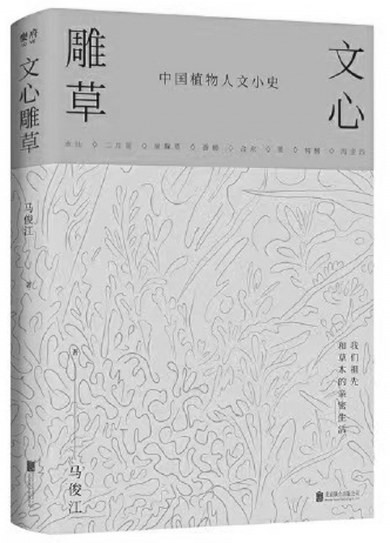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