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就拿到了刘进宝老师的《敦煌学记》,当时就有要为这本书写篇书评的冲动。书中文章既是刘老师对敦煌学的认识,又有他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因缘,不经意间透出了他对百年来敦煌学的学术、事件与学人的情感。这份情感,颇为动人。
容易亲近的敦煌学
敦煌学虽然是国际显学,既时髦又普及,但它同时也给人以高深莫测之感,非常人所能置喙。因为哪怕“什么是敦煌学”这样平常的问题,不用说普通人难以明晓,就是专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专家,也还各有所执。
本书第一篇《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和研究对象》(第1-14页),将这个关键问题铺展到读者的面前。作者指出: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和1930年中国学者陈寅恪分别提出“敦煌学”一词,但当时学者们都研究敦煌文献,后来又扩展到敦煌石窟艺术,并未对其属性、含义和范围给予足够关注。1981年,随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一说法的误传,国家相关部门开始调研,拟成立相关研究机构。1983年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敦煌学讨论会。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对敦煌学的概念及学科建设展开了讨论。姜亮夫认为一切与敦煌有关的文物都可以纳入敦煌学之中,而周一良以为敦煌资料虽然异常丰富,但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前者失之宽,后者求之严。其他学者也各有所重,至今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作者认为,在东方学背景下诞生的敦煌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地名学的国际显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能够成立的,其研究对象是敦煌文献、敦煌石窟、敦煌史地和敦煌学理论,它围绕敦煌展开,但是研究者不能局限于敦煌,要与敦煌学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学科和资料融会贯通。通过作者细致的学术史梳理,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敦煌学产生、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国际局势与学术发展的紧密联系。
在将什么是敦煌学铺陈给读者之后,作者接着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一学术史公案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梳理,揭示出在198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由于当事人误传而造成的说法,在中国的流传促进了学界的反思,并在国家支持下推动了敦煌学的快速发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提出及其反响》第15-28页)。
而敦煌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显学(《敦煌学何以成为国际显学》第62-68页),除了敦煌文献自身的关系之外,与敦煌是丝绸之路咽喉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地位》第29-38页,《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敦煌与莫高窟》第38-49页),也与它丰厚的历史文化层积有关(《“五凉文化”孕育下的敦煌学》第50-61页)。
但是敦煌瑰宝的发现过程,却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件充满了悬疑的伤心史。1900年藏经洞被道士王圆禄发现后,不断被盗窃(《敦煌宝藏是如何被盗的?》第86-98页,《华尔纳敦煌考察团与哈佛燕京学社》第99-107页),敦煌瑰宝流散世界,以至于藏经洞的发现经过及相关问题都成了敦煌学上的难解之谜(《千古之谜谁解说? ——敦煌藏经洞封闭时间及原因讨论综述》第69-86页)。
上述话题,都是关于敦煌学最核心的话题,作者围绕这些话题娓娓道来,让读者对高深的敦煌学能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还一份温情给敦煌学
敦煌学的发展,离不开几代敦煌人的坚守,离不开几代敦煌学者的努力。其中有艰辛,也自有温情。
1943年1月18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宣布成立,是年3月,常书鸿到敦煌,开始研究所的建设工作;1944年1月1日,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1950年8月1日,该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1984年1月15日,在原来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宣布成立……敦煌研究院的历史,一方面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一方面有着几代打不走的敦煌人的坚守。(《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缩影与标志》第108-119页)在这些敦煌人中,既有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常书鸿、樊锦诗,也有敦煌学者才熟悉的孙儒僩。他们并非天生就爱敦煌那艰苦的生活,也并非天生就坚强,而是对文化有虔诚的信仰。
刘进宝先生在写敦煌人的时候,不仅看到了他们的辉煌,更看到了面对敦煌的艰苦生活,以及人生的磨难中,在敦煌的他们也有犹豫,也有彷徨。如评《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时,特别检出樊锦诗1963年北大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敦煌时,不想去敦煌;在到敦煌工作时,曾感到孤独,觉得世界都把她忘记了,北大把她忘记了,老彭(她爱人彭金章)把她忘记了;1968年父亲受批斗去世后,她也曾不断思考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在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孩子缺乏照料时,她也曾动摇……但是,最终她还是将生命融入了敦煌(《她已将生命融入了敦煌》第174-188页)。
敦煌学人遍布中国,既有身处大都市、在著名学府者,如北京大学的荣新江(《一位学者的成长与一个时代的学术》第216-226页,评荣新江《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也有僻处边地、在普通高校者,如天水师范学院的张鸿勋(《张鸿勋先生与敦煌俗文学研究》第153-173页),还有广大的海外学者,如日本京都大学的高田时雄(《日本所藏敦煌文献的来源及其真伪》第189-205页)……他们都是敦煌学学术史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铭记为敦煌学发展做出贡献的所有学人,是还一份温情给敦煌学。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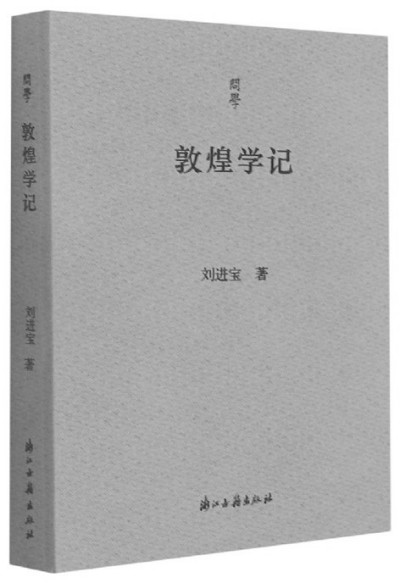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