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而优则士》一书有一很醒目的副题:“《世说新语》三十六计”,我正是冲着这一书名优先来拜读此书的。现在“标题党”大行其道,令人敬畏;但一本学术著作总不至于在书名上玩什么惊悚夺人的花样吧,著者一定是把《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们都看成是老谋深算、长于表演的有心人。这倒是非了解一下不可的。
著者说:“在本书中,我将通过仔细研读文本,从八个方面对魏晋名士在公共空间中的‘表演’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剖析他们思想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第42页)书中一反传统的意见,指出魏晋名士的风流洒脱、放荡不羁并不代表他们的真性情,也不是什么“个性的觉醒”,而更像是一场场经过精心谋划的“表演”,需要“观众”看到并广为传播——他们借助这种手段来谋求更佳的社会性利益,如声誉、地位、官阶等等。所谓名士“风流”,只不过是一种精心的策划。书中就此多有深刻的细读和有趣的分析,许多片断精细入微,明察秋毫之末,读来令人眼界大开。著者学兼中外,文献精熟,旁征博引,无不头头是道,深中肯綮。像这样充满新意、发人深思的大著现在并不多见,非常值得欢迎。
应当承认,确有某些魏晋名士工于心计,他们的若干言行带有做秀的性质,其“风流”的背后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奥妙。此事过去也曾经有学者指出过,鲁迅先生即明确地说过“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但是像《演而优则士》把这种两面性扩大到全体魏晋名士,扩大到《世说新语》所记录的全部言行,说“名士皆演员”(第39页),“魏晋名士人人都渴望通过‘表演’获得赏识”(第45页),又认为该书的三十六门很像是名士们的“三十六计”,这样的结论似未免以偏概全,难以起信。
《世说新语》的第十八门是《栖逸》,这里的苏门先生、孙登等名士远离体制,走向山林,他们还要谋求什么世俗的声誉、地位和官阶? 第十九门是《贤媛》,那时的女流之辈中的强人,即使谋略再妙声誉再高也进入不了官场。
一般意义上的名士恐怕也不至于处处刻意表演。《世说新语·雅量》第二则载,前中散大夫嵇康在被执行死刑时的表现是——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先前有一位朋友袁准(字孝尼)请嵇康教他琴曲《广陵散》的演奏,当时嵇康不肯教他,此时便忽然发了这么一句感慨。这样的“表演”能谋求到什么社会性利益呢。死到临头了,嵇康不仅“神气不变”,还要弹一曲《广陵散》,这是何等的风度!
两晋之交的大名士卫玠(字叔宝)是著名的美男子,清谈的水平也非常之高,《世说新语·文学》第二十则载:
卫玠始度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卫玠简直不去理会作为主人的大将军王敦,只是同另一位名士谢鲲(字幼舆)通宵达旦地清谈,结果生了一场大病。卫玠告别王敦、谢鲲以后到了豫章,作为著名的美男子他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围观的人极多,他的身体本来就很弱,“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此即所谓“看杀卫玠”(《世说新语·容止》第十九则)。卫玠是当时明星式名士中的一个悲剧型人物,他在上述大小不同之两种公共空间中的表现,总不至于是在玩什么谋略吧。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也就不必多举了。
过去搞政治运动,对人的处理多有扩大化的问题,教训很深;在文学研究中从事文本诠释,特别是在讲究理论先行的路线之下,看来也很容易发生类似的问题——虽然可能达成某种片面的深刻,但较难站稳致远从而大有益于学术。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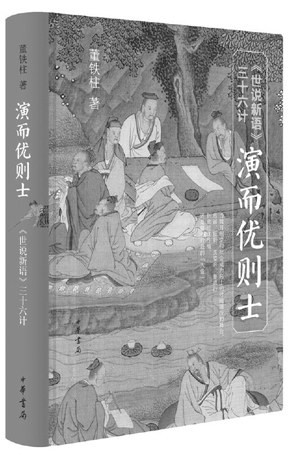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