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小苗(我习惯这样称呼苗德岁教授)写的一篇关于达尔文的短文在《中国科学报》上刊登。像往常一样,我把它剪下,收藏起来。近期与小苗通信时,我建议他把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达尔文和演化论的零金碎玉文章,汇集成册,整体出版。他回复说,译林出版社已在筹备出版他的新作集,这让我喜出望外。
我认识小苗已近半个世纪。初识是在1975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作为南京大学地质系地层古生物专业的学生,应约徒步从汉口路校舍来我所参加乒乓球友谊赛。1978年夏,我到内蒙古考察,路过北京,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集体宿舍小住,走廊上巧遇小苗及其学友,他刚通过“文革”后首次研究生入学考试被录取。晚上,我们在屋顶大平台乘凉,一边遥望闪烁的星星,一边山南海北地畅聊,相谈甚欢。他的一篇文章前几年(1975年)在《化石》杂志上发表,听说领袖想看该杂志,杂志印出了线装大字本。我说:“主席可看过你的文章喽!”那时,我们都知道他的文笔很好。后来,虽说都研究古生物,却因门类不同,地层不相邻,他又去了美国深造,我们相隔于大洋两岸,鲜有联系。20世纪90年代初,他应金玉玕老师邀请来我所开放实验室讲授如何写好科技英文,我们又开始接触。他英文很棒的名声早已在外,所里同仁和我时有向他请教如何把握英语用词,他都尽力帮助。2007年,经张弥曼老师推荐,中科院院士工作局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请他翻译由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研究院撰写的《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一书,周光召先生写了序。2010年起,他花了足足两年时间,倾情完成了达尔文巨著《物种起源》第二版(译林出版社“译林人文精选”版,2013年)的翻译。2012年,他应邀来所做“达尔文与《物种起源》”讲演,加上他还兼任《古生物学报》、Palaeoworld (《远古世界》)海外编委等职,多次来所访问,通过频繁的交流,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在翻译《物种起源》后,小苗应多家报刊、新媒体邀请,开设了“达尔文之光”“科学源流”专栏,通过专访、书序、书评等多种形式,介绍自己研究达尔文的心得。从中,他挑选出24篇(包含时论、序跋、书评、随笔、散文等不同体裁)汇编成册。这些作品均与达尔文和演化论有关。小苗为什么要写一位一百多年前离世的英国人查尔斯·达尔文呢? 这里原因很多。我想,至少有两个。第一,翻译巨著《物种起源》给他带来的激情,搅动了他酷爱达尔文的澎湃内心。第二,达尔文演化论事关我们人类认识世界和生命的最根本的问题。20世纪早期,国内先贤对达尔文演化思想的传播,使中国成为民众接受演化论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人对演化论的认识多一知半解,以讹传讹,“鲜有继承与发展”(鲁迅语)。人们常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挂在嘴边、写在书里,同时却对之有较多的误读和误解。例如,很多人以为自然选择就是“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社会上过分渲染和强调“生存竞争”,夹带了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后来,囿于社会、历史、政治等因素,有关达尔文的科普文章在国内甚少。小苗读过不计其数的有关达尔文的外文书籍,对达尔文的了解和对演化论的认识是他写好这些文章的基础。为正本清源,改变误识,小苗认准从孩子着手,立志在达尔文和中国青少年之间架起一座知识心桥,“为儿童普及经典,让经典亲近少年”。他把深奥的生命演化理论知识普及给孩子们,并把这种普及看作一种乐此不疲的劳作。“小荷才露尖尖角”,他期盼的是满湖映日红。这次,将散落在四处的有关达尔文及其学说的短文收编成册,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方便快捷集中阅读的机会。
读小苗的文章愈多,我愈感到他与达尔文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穿越时空的缘分。从他考研究生,面试主考官周明镇先生在口试环节问《物种起源》一书的中英文书名全名是什么时,这段缘分就在冥冥中开启。20世纪80年代他初到美国购买的第一本书就是《物种起源》。他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哺乳动物化石,也就自然而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生命演化的问题上。再到后来他下决心答应并倾情精心翻译《物种起源》、创造性地编著达尔文和演化论的少儿读物、饶有兴致地撰写关于达尔文的短文,一路走来,他已与达尔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何估量达尔文说服大多数人改变长期形成的固有信仰的拨乱反正力度? 为何要把《物种起源》的第一、第二版而不是第六版译成中文? 这部巨著的写作背后还有多少你不知道的细节?为什么说达尔文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植物学家? 为什么从达尔文身上要引出“为学如筑金字塔,根基要宽顶要尖”(胡适语)这句话? 相信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读者将会开启一段愉快的探索达尔文之旅。也许这就是小苗想为“达尔文学”(Darwinology)做出的贡献吧!
小苗年轻时,酷爱看书,中文功底好,有一颗向往文学的心。他有两个令人羡慕的特点:博览群书和记忆超群。他一直把选择性地读书看作生活的第一需要,这使他对中西方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他对达尔文情有独钟,凡是遇到涉及达尔文的新文、新书,他都会眼睛一亮,紧抓不放,一探究竟。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写作中,他超强的记忆力发挥了作用,写到关键之处,哪位名人在何时说过的什么话,信手拈来,放置得恰到好处。他对达尔文崇拜得五体投地。他说:“达尔文那时并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研究条件和知识基础,却能写出《物种起源》这部伟大著作,太了不起了。”19世纪达尔文撰写的这部巨著,用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典雅的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的文学语言,很不好懂,原汁原味地把它翻译成中文,真是难上加难。他能成功翻译的根本原因是“驾驭英语文字的功力”和“用英语表达非常复杂的概念的技巧”(他的美国导师语)。熟悉他的几位美国教授都欣赏他这方面的才华。我记得忠和(指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周忠和——编者注)说起他自己在美国读博的四年里,小苗与马丁教授海阔天空地“摆龙门阵”的场景(广涉天文地理、历史政治、艺术宗教、人文轶事)。小苗尽管英语很棒,翻译时却丝毫不敢怠慢,他“如履薄冰,未敢须臾掉以轻心、草率命笔,始终坚持忠实于原著、保留原著全部精华”的翻译原则,展现了他认真、严谨和审慎的态度。
小苗作为专业学者热衷于科普创作的初衷,还得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后,他的美国导师在一次聚会时说:“苗的博士论文研究漂亮、文字优美,可惜读它的人,全世界不超过一打(12人),能读懂它的人,不超过一只手(5人)。”导师不经意的一番话,却深深地埋在他心里挥之不去。出于多种原因,小苗从事科普创作已临近退休时光,可他还是下决心要发挥余热。特别值得赞扬的一点是,他是用做学术的态度和方法来做科普的,任何一件事情、一个出处、一个地点、一个时间,都把来龙去脉搞得一清二楚。否则关键节点弄错了,定会以讹传讹,这在《马克思与达尔文的交往》一文里有明显的体现。他说过:科普这块阵地,科学家们不去占领,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势力就会去占领。他希望写给青少年的科普书,也是写给中老年读者的书,还是写给非专业读者与专业同行共读的书。因为他心里有一个目标:争取做到“大人读了不觉浅、少儿读了不觉深;内行读了不觉浅、外行读了不觉深”。这就是小苗给科普创作树立的标杆。
小苗是一位高产、高质量的作家。短短十年内,他出版了超过二百万字的作品。读者可能不知道他是在怎样的身体状况下写就的。在夜以继日地完成达尔文《物种起源》(2013年)巨著的翻译和原创性科普读物《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2014年)不久,2014年底,他不幸得了脑卒中,半身麻木,举步维艰。他面前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消极躺倒,二是康复治疗、奋起继续创作! 他毅然采取积极的人生态度,下决心要与时间赛跑。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凭着坚忍、顽强的毅力,仅用一只右手,五年里,他又连续完成《天演论》(少儿彩绘版,2016年)、《给孩子的生命简史》(2018年)、《物种起源》(插图收藏版,2018年)、《自然史》(少儿彩绘版,2019年)和《物种起源》(精编导读版,2020年)文稿等,还忙里偷闲、有感而发地写了那么多部科普文章。尤其是在创作《给孩子的生命简史》这本科普读物时,为了超越自己、写出新意、朝“科学性、文学性、趣味性”这“三合一”的方向努力,他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付出了多少时间和心力。2019年深秋,他来我所访问,当他步履蹒跚、拄着拐杖艰难地登上二楼,来到我办公室时,我心中五味杂陈,感佩之情油然而生!
有人夸奖小苗是当代的高士其。我想,他是一位特立独行、文理兼修、酷爱达尔文、谙熟演化论、乐意把熟知的科学领域的优美风景介绍给行外人的古生物学家。经历过特殊年代,烙下了特殊印记,成就了不可复制的他。
本集短文篇幅不长,清新可人,文笔流畅,优美生动,诙谐有趣,既硬核又通俗,既理性又文艺,知识面广,可读性强。成书出版在即,先睹为快之余,特此倾情推荐。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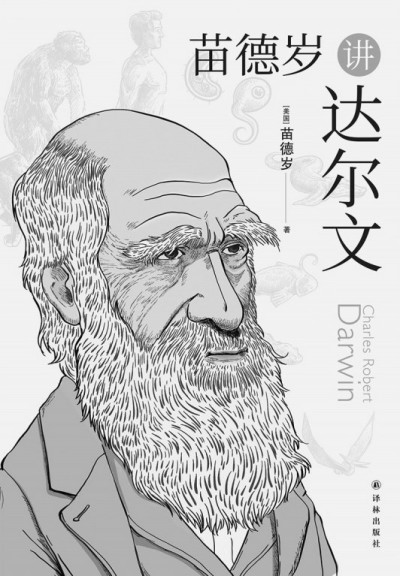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