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论及颜色,首推红色,有道是“中国红”。红有赤、朱、丹、绛、绯等近义词,从深到浅,概指不同视觉效果的红色。考古发现,古人类的墓葬中多有赭红色粉末,经鉴定为自然界中的赤铁矿,其因含铁量不同而呈现不同程度的暗红色,赭石因此被称为世界上第一种颜料。
“画家惟红色最难著”。明代李开先《中麓画品》记录一则画坛逸事,说后世浙派山水画的鼻祖戴进“独得古法”,擅长画红,他在《秋江独钓图》中画一红袍渔夫,垂钓于江边,视为得意之作呈上。不料遭《杏园雅集图》绘者谢环差评:“画虽好,但恨鄙野。”上也批判道:“大红是朝官品服,钓鱼人安得有此?”并对其画作再也不看,导致戴进在京城境遇不堪。要说戴进之失,应是他未遵循谢赫六法之“随类赋彩”,本该是乡野灰,却画了个朝官红,显摆却落为败笔。若把形与色视作古典审美的重要坐标,那么俗语“一白遮百丑”则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颜色比造型更影响视觉效果的道理。
由郭廉夫、郭渊合著的《中国色彩简史》围绕色彩在中国艺术史上的演进,从文化史角度观照中国艺术的发展,以史前岩画、远古彩陶、髹漆器具、敦煌壁画、丝绸锦绣、传统绘画、宫殿建筑、木版年画等丰富的图像为例,从五色系统论及对后世之影响,从历代文论中阐述的传统色彩观,尤其从材料、技术、工艺等方面梳理色彩史,从制作实践到文化交流乃至伦理规范探寻色彩美学的规律,展现出一部绚丽多彩的中国艺术史。
色彩:中华美学体系的重要脉络
就色彩学而言,本书开篇从色彩的自然属性论及早期文明的工艺技术,对史前时期彩陶、漆器、岩画的色彩进行了简要描绘,在对先秦时代的青铜冶铸、丝绸练白、织物染色做了具体介绍之后,便逐步深入到色彩的伦理规范阐述。
“色彩的呈现与表达,越过了文字、颜料、典礼仪式、日常生活等表象,持久地展示着人们审美、文化、思想的水准。”中华自古即有五色之说,据《尚书》记载,公元前两千多年的禹与舜对话就谈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礼记》已规范起西周至汉初天子衣食住行的色彩礼仪之道。《考工记》将五色与空间方位相关联,定为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黄,后经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五行学演绎,逐步形成影响后世的五行五色系统。青为首,赤为荣,黄为主,白为本,黑为终。
彭德先生前有专著《中华五色》,将青、赤、黄、白、黑五色从色象、色类、色兆、色界四章二十节进行过系统梳理。本书对此仅为概述,其创新之处倒是作者认为《周易》的贲卦首次提出了光的装饰作用,“贲于丘园”“白贲无咎”,绚丽复归于平淡的白贲之美,被宗白华先生视为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
本书还对孔子“绘事后素”提出新解。作为我国绘画使用色彩的最早文字记载,这句话被朱熹《四书集注》“权威”地解读为绘事“后于素”,作者则根据1979年江西春秋战国崖墓中出现的双面印花麻织物上印有白色花纹一例,推翻朱熹之说,认同郑玄对《考工记》“画缋之事后素功”的注释:“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
本书较为集中地梳理了先秦诸子百家的色彩观,无论是孔子的“恶紫夺朱”,还是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知其白,守其黑”,或是庄子的“五色不乱,孰为文采”,孟子的“白雪之白,犹玉之白与?”,作者探寻影响中国艺术的思想智慧与传统文化的底色,从色彩角度重构了中华美学体系。
光彩:传统艺术史论的科学叙事
公元1666年牛顿发现光谱的七色现象,现代色彩科学理论得以奠基。可以说,色彩的艺术属性与科学属性缺一不可。有别于传统美术史论气韵生动类的程式话语,本书对色彩史的研究方法非常注重科学分析。譬如讲到远古彩陶,即列举彩陶颜色现代光谱分析表,将不同陶色与着色剂材质、烧制温度进行化学角度的论述。“史前我们的祖先用赤铁矿粉,赭石和氧化锰等做呈色元素,在陶坯的表面描绘图案,经窑火烧制成赭红和黑色等颜色纹样的彩陶。”
再比如论及青铜器的金银错工艺制作流程,详细列举原材料配方、纹饰烧制办法、刻镂加工处理等步骤,颇似一份条理清晰的实验报告。
这种科学叙事的特点还体现在作者解读某些重要颜色外来源头时的开阔视野中。“13世纪的蒙古汗国将来自伊朗的苏麻离青(钴青料)用于中国瓷器上,由此产生了元青花”,“1500—1600年,胭脂虫红由西班牙人生产并垄断,通过国际贸易传入中国”……宛如探索发现类科普纪录片的口吻。
华彩:以图证史,织彩为文
本书一大特点是配有大量图片。从彩陶到青铜器,从帛画到刺绣,从《韩熙载夜宴图》到西王母寿宴浮雕漆屏,全书以图证史,通过二百余幅历代经典艺术品中的色彩之美,打通色彩史与艺术史,展现了从艺术图像探寻文化脉络的学术理路。
值得一提的是,正文后还有十一则附录,包括《辍耕录》中颜色名称、明清琉璃窑釉料配方、历代服色、敦煌壁画颜料成分,以及一份色彩史年表。这些文献都有助于美术研究者按图索骥继续探寻色彩奥妙。
《六书故》云:织彩为文曰锦。从《考工记》、唐锦到釉料配方,从敦煌壁画、蓝色琉璃到月华裙,本书以独特的视角、科学的论述、典型的图像梳理了绚丽多彩的中国艺术史,织就了一幅中国色彩的锦绣华章。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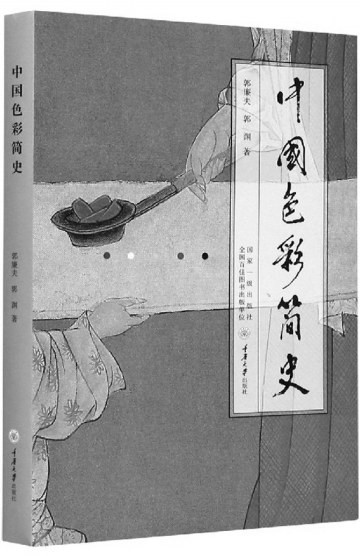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