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佛道二教之关系具体体现在其与天师道以及白莲社、慧远的关系上。如果能把陶渊明与佛道二教关系阐释清楚,对于探究陶渊明思想来源与构成、认识陶渊明思想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及其诗文风格成因,均将大有裨益,进而可以有力推进当代陶学研究。范子烨《五斗米与白莲社:对陶渊明的宗教文化解读》,正是基于以上学术目的展开的探索。
本书上篇,重点讨论陶渊明与天师道(“五斗米教”)的关系。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指出:“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尊天师者也”(《金明馆丛稿初编》)。但是,陈氏观点却在一段时间内被人忽视了,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反响。作者沿着陈寅恪首倡的观点,集中全力研究陶渊明与道教特别是与五斗米教的关系。作者沿波讨源,搜集大量丰富的原始材料,通过对“陶渊明的服食养生与‘临终高态’”“从家族看陶渊明的宗教信仰”“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与浙江天师道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论证,以及陶渊明喜欢种植药材、喜欢饮菊花酒,重视服食养生、陶诗中对菊花的诸多描写等具体现象的揭示,最终证明陈氏关于陶渊明是天师道信徒的观点是正确且慧眼独具的。作者进而指出:服食养生是中古时期流行的时尚,辞官后的陶渊明作为一位庐山脚下的老农自然也不例外;陶渊明的斜川之游及其诗作,明显地模仿王羲之兰亭雅集,而兰亭雅集“属于当时浙江天师道的一次群体性活动”。陶渊明的《饮酒》《止酒》《述酒》等涉及饮酒的诗作,体现了一种“是自然非名教”的意旨,与其家族世袭之五斗米教信仰密切相关。凡此种种,皆可证明陶渊明信奉天师道,从而丰富了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作者认为,从主要倾向上看,“陶渊明是反对道教的神仙不死、长生久视之说的。这说明他对自己以及自己家族世袭的天师道信仰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道教自身的理论和思想有所超越。”所获结论科学客观,合情合理,令人信服,陈寅恪先生学术观点的当代价值由此得到体现,并给后人以深刻启发:“一位伟大诗人的历史真面目由此局部地加以彰显,而一代学术巨擘的伟大成就由此亦可见一斑。”经过切实的努力,作者终将陈寅恪先生八十年前的空谷之音铸成今天学术界的坚实回响。
本书下篇,重点讨论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作者旁搜远绍,深入探究陶渊明与庐山“莲社”包括“虎溪三笑”故事的历史真相,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这些流传甚广、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至中唐时期才开始出现,实际上是后人的妄附和臆造,表明的更多是一种文化心态。作者也从陶渊明与慧远生死观迥异之角度,证明陶渊明不可能栖心释迦。作者同时认为,在文学创作上,陶渊明对佛教文学有所接受。以《闲情赋》为例,作者指出,《闲情赋》中震撼人心的“十愿”,“标志着‘愿’的集中化、系统化和条理化,这与佛家的名相——‘十愿’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佛家的“普贤十愿”给陶渊明以深刻的启发,陶渊明“巧妙安排,精心设计,在吸收前人同一题材文学创作的艺术营养的基础上,赋予“十愿”以世俗生活的内容,那就是对爱情的表达,对女性美的歌颂。其他例证尚多,兹不一一。本书下篇的论述缜密而辩证,体现出作者鲜明的学术个性。
总的来看,本书论题集中,作者目光敏锐,紧紧抓住陶渊明宗教文化的实质内容——五斗米与白莲社予以阐发,探骊得珠,倾昆取琰。本书讨论的问题看似具体而微,但其意旨却极为宏富,彰显出方法论的启示:经典的学术观点永远不会过时,只要深入其中,就会大有收获;论题的选择不怕微小,就看论述得深刻与否,有没有悉心揣摩的一己之得;竭泽而渔地搜集材料,其论据才会充分,论述才能周详。作者说:“就目前的研究而言,我已经穷尽所能见到的所有文献了,不知以后是否会有新的材料补充。我相信自己没有‘误入洄水沱’。”正因如此,作者才能将相关文献的蛛丝马迹予以贯通,从而还原历史真相。本书语言典雅深沉、从容不迫又不失华彩,在激情回旋的诗意中呈现出理论与逻辑的力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作者在本书自序中云:“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将陶渊明及其作品中‘佛道的成分’明确地‘分析出来’。我特别喜欢研究难度大的问题,因为其中可能蕴藏着更为重要的学术史和文化史意义。”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是不敢做如此选择的。经过科学缜密的考辨,作者成功打开一个陶学研究的新视界,蕴大含深,风光无限!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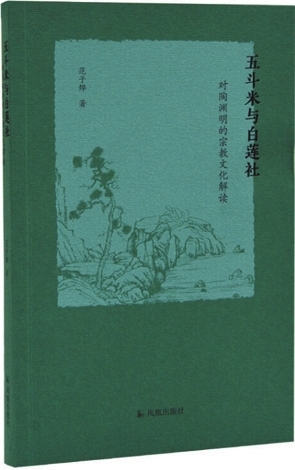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