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范今先生的《人文言说》《舍下论学》新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对于史学化方法凸显而宏观的文学史整体研究日见沉寂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事件。孔老师向以文学史宏观研究见称于学界,国内第一部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命名的著作便出自孔老师,后又以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了自身的文学史观。新著中既有以往受到大家普遍关注的文学史论的严整论文,也有像《舍下论学》这种不拘一格、自由出入于文学、历史与文化之间的述学实录,后者可以说颇具《论语》神韵,孔老师自身作为孔子后裔的文化基因也外化为这样一种古今会通的论学实践之中。
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都知道,孔范今先生是一位始终站在高处,能够产生自主的学术思想的学人,这与孔老师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总能保持一种与既有研究展开持续有效且深入有力的对话是联系在一起的。举例而言,“五四”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焦点论题,也是衡量这个学科研究生态和研究水准的一个话语场。孔老师较早地将“五四”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不同于不少人将“五四”仅仅作为一个学科对象,也有别于一些学者将“五四”视为某种价值标尺甚至价值终点,孔老师很早便将“五四”拉回到阐释起点,重新辨析“五四文化模式”,在新著中也有关于“五四”“文化其表、历史其里”的辩证,有效地扭转了不少人在“五四观”上的认知错位和价值迷思。近年来,孔老师又不断讨论“新人文主义”的义理,其实也是将“五四”式的人道主义思潮作为一个对照来谈论,也就是要重新追问启蒙理性、科学伦理的学理缺失,而这又是在充分顾念“五四”历史叙事的时代合理性的前提下展开的。可以说,孔老师的“人文言说”与这些年来一些有关现代性批判的话语、那些对于法国启蒙运动与苏格兰启蒙传统这二者不同的辨析、对启蒙现代性与浪漫主义的现代性的分殊等等,实际上都已形成了某种有机的对话。
文学史研究历来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孔范今先生学术工作的一个重心。相较之下,孔老师是少有的真正具有自己的文学史观的学者,当年在“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后,在较长时间内并未出现真正的重写实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研究者尚未建立起新的文学史观,有的只是在价值立场上有所颠覆,但在研究范式上又缺少新的建构。孔老师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导论中,从不同侧面完整论述了有关文学史命名与断限、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历史的单向突进与文学的补偿式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了“历史结构说”。正是具有了这种自主的文学史观,孔老师才能走出那种简单的个案重估与价值迷恋,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学史论域。史观的建立也有助于文献工作的有机性,我们当下都在讨论史料研究与理论阐释、问题意识之间的张力,而孔老师当年也做过出色的文献考辨与挖掘工作,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曾经大大推进了建立完整的学科对象世界的进程,而随后的《中国现代新人文书系》《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等也都是文献史料研究的重要收获。值得注意的是,孔老师的文献梳理始终没有脱离他的文学史的整体研究,而且最终内在于其“历史结构说”和“新人文主义”思想创辟之中。此外,孔老师在新著中也有不少有关当代文学的言说,联想到近年来“现实主义”问题的回潮,虽然语境不同,但不难发现孔老师对于两种现实主义的论析颇具学术预见力。《舍下论学》回归到许多基本的学术问题,比如何为文学、何为文化等,也都让人觉出孔老师是带着丰厚的文学史研究的积累重新进入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当然,两本新著也为我们留下了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对文学的本质化理解与文学自身的历史化品格之间的张力?卡勒曾说,文学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话语,是为了揭示自身的有限性而存在的艺术机制。文学既表现意识形态,又一再解构某一确定的意识形态。新人文主义也是一种话语建构,相比而言,文学的边际远远大于任何一种已成的思想的边界。文学就是为了打破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秩序而存在的。尤其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她的发生发展都始终与历史进程相关联,而生命直觉与情感本能常常与文学的历史关怀相互催生、相互转化,甚至是一张纸的两面,失去历史相关性,文学的人学色彩、诗性意蕴也会变成空心化的知识生产的结果。总之,如何将新人文主义视野之外的文学史对象有机地、内在地纳入文学史叙事之中,而不是重新陷入某种二元对立式的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之下,这也是一个值得反复考量的问题。孔老师多年前便已提出“历史结构论”,其实也正是某种整合的尝试。进一步而言,对现代性的反思往往在学理上易于阐发,但在肉身实践层面却又很难贯彻与坐实。我们可以在学术话语中反省直线发展的进步主义,但在日常世界中、甚至在学术共同体的现实语境中,却又很难摆脱强调事功的历史现代性的裹挟性影响,我们能够给郁达夫式的颓废主义以美学意义,却常常忘记颓废也是一种日常意义上的现代性,也是抵抗科学理性霸权的肉身实践的一种型态。可见,孔老师提出的新人文主义不仅是一种学理价值,也是一种有待检验的实践立场,能否以此打破理性主义的分别心,能否怀抱真正的生命同情之念度人量物,将是我们在学术内外均应谛视的目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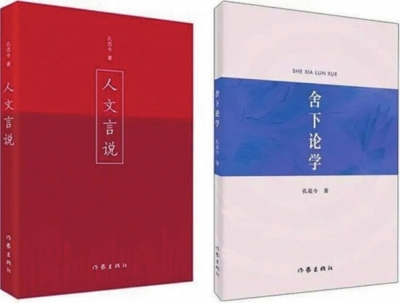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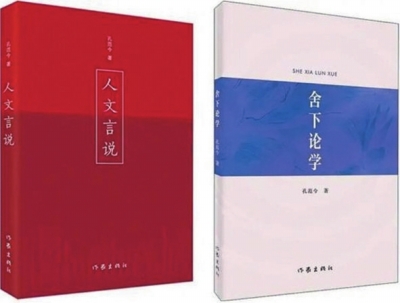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