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大体量且厚重的优秀长篇小说,《有生》所表达的东西是极丰富的,是多维度的,故事中隐含着事件性,不可轻易概括、总结和归类。
《有生》所呈现的,比人们日常谈论的现实更辽阔、也更真实。小说起始于主人公祖奶躺在床上的回忆,也终止于祖奶的回忆。从晚清到当下,上百年的时间跨度里,几十个生动的人物,在祖奶一天一夜的讲述里,鲜活地出现在读者面前。祖奶乔大梅、如花、喜鹊、麦香、罗包、钱玉、宋品、毛根、白礼成……他们是农民、手艺人,靠苦力刨食,在日复一日的苦难岁月里,释放着个人的喜怒哀乐与生命悲欢。
小说的开头,乔大梅十岁那年,在锢炉匠父亲的带领下,自河南的虞城逃荒北上,他们的目标是京城,父亲想送她进宫当细匠,但时事激变,这不在这位锢炉匠的料想之中,还没到京城,民国就取代了大清朝。京城成了不安之地,于是,父女继续北上,逃荒途中,父亲听说塞外一个烧饼就能换一亩地,他们便被能拥有土地的梦想吸引,来到了故事的发生地营盘镇宋庄安家落户。
历史不会关注小人物,我们的历史书里写满了宏大叙事,写满英雄人物与关键事件,千百年来,普通人的命运被宏大叙事淹没,甚至连一个叹息都没有留下。好在文学作品让我们的目光注意到了这些历史的角落,有机会感受大历史中小人物的悲欢。胡学文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形象“祖奶”,为中国乡土文化写下了灿烂的注脚。《有生》的主人公是祖奶乔大梅,她是一个接生婆。小说中的祖奶形象,是一种超越生死的象征性存在,她把接生当作天职,一生共接生了11986个人。接引生命是祖奶的天职,又是她的生命源泉。祖奶虽历经劫难,见惯生生死死,尝遍人生沧桑,但仍屹立不倒,数次站在死亡边缘,她都被接生的强烈愿望给拉回现实。借助祖奶这个人物,胡学文表达了对生命深沉的关怀,自始至终,作者都在用文字思考着“何以为生”的问题。只要还活着,就不能放弃,就绝不屈从于人生的艰难,甚至不屈从于各种不幸,积极面对人生,在苦难中坚毅而不气馁,悲伤而不绝望,是人生最好的态度,一个又一个难过的坎,一场又一场难以避让的苦难,对许多人来说,那是活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接生过上万个孩子,没有一个是笑着出来的,恰恰是哭声证明了生命的诞生。”这是祖奶的生存哲学,更是作者对生命的认知。
这部小说出版后,面对记者的采访,小说家胡学文说,《有生》是一本教人“怎么生,如何活,如何走出人生困境”的小说,“我写的是生和活,生是开端,活是过程。”
现当代文学史中,表现女性在生产生育上苦难的作品并不多,但胡学文以一个男性作家敏锐的、强大的同情心,理解女性的痛苦,强调女性的价值,让我们在当代文学史上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形象“祖奶”。祖奶碰到的每一个接生案例,都让我们近距离地看到了母亲的苦难,原来“生”是如此不易,如此艰辛和危险。读《有生》,每一个生命的到来,都有孕育和生产的艰难,我们不仅理解了生命本身的困难、接生的困难,更理解了女性群体的困难。女性承担了“生”的重任与苦难,但千百年来,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命运并未因此而得到重视,反而会因为生育而致困、致贫。
因生育而致困、致贫的情况,即使在当代女性身上也比较常见,生育是女性的苦难,但不能生育,或者是不能生出男孩,在常识眼光中,是女性更大的苦难。小说中,祖奶的女儿不能生育,在一个接生婆身边最亲近的人身上,看到女性因不能生育,给她个体的命运带来了巨大不幸和苦难,在这些方面,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对女性报以极大的同情,第一次在乡土小说的写作上把女性当作主人公,把女性的苦难描写得如此淋漓尽致。这是极难能可贵的。
即便不谈《有生》在小说艺术上的不凡成就,以及复杂时代中各种人物生存的艰难和苦难,也不去谈小说中小人物们丰富曲折的情爱生活,仅就小说中关于女性在生产中的各种遭遇,读者,无论是男性读者还是女性读者,都会重新去理解和看待女性命运。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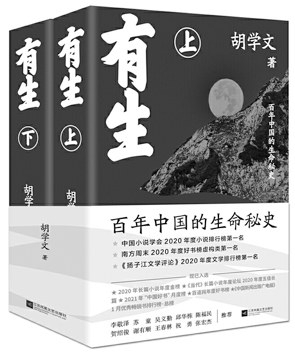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