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北方有棵树》,最直接的印象是,此书充满了浓浓的文卷气。对于有些读者,或许会产生一种有趣的阅读体验:有时候,书中的描写和抒情首先令人联想到的,不是彼时彼刻作者置身的那个具体的物理场景,也不是自己曾经历过的某一个四季更迭的间隙,而是某个文学片段,某件艺术作品激发的意象。
《北方有棵树》的这种特质,更具体地表现在行文中,是作者欧阳婷在自然场景中信手拈来地引经据典。仅仅翻阅两下,读者就可以轻松列出一大串书中频频出现的文学和艺术大师名录:贝恩德·海因里希、南茜·罗斯·胡格、约翰·巴勒斯、贝丽卡·索尔尼、华莱士·史蒂文斯、利奥波德、普里什文、西蒙·巴恩斯、罗伯特·麦克法伦、帕乌斯托夫斯基、华兹华斯、约翰·缪尔、张爱玲、卢克莱修、泰戈尔、村上春树……通读下来,作者提到的创作者少说也有五六十个。
再看此书的结构——按月份展开,追随着许多自然作家谋篇布局的策略,如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西蒙·巴恩斯的《聆听》和爱德华·格雷的《鸟的魅力》,以充分呈现季候与生物之间的关联。作者的笔触和构思之间,无数次令人联想到《醒来的森林》《怎样观察一棵树》和《野果》中的类似口吻。“隼自云层降落”这一篇简直是对“隼”这个主题的阅读随笔,而最后一章“不管你多么孤寂,总有风景能抚慰心灵”则直接是一篇《心灵的慰藉》的书评。
毫无疑问,作者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人文型博物学家”,或带点调侃意味地说,一位“书呆子型博物学家”——作者对此不仅高度自觉,而且绝不孤独。哲学家走向荒野,读书人漫步林间,早有悠久而丰富的传统。作者受此传统的滋养,并以这本书作为回应。正如她自己所说,自然写作对她,并非“是一个特殊于其他的类别,阅读,精神生活的求索,文学的、电影的、艺术的影响,等等,它们仍然像一股深厚而隐形的合力,把我自然而然推向道路未知的前方”。
因此,我们也可用作者的摘录作为线索,来看看这条路上的风景何以抚慰人心?
“小津安二郎式的画面”
作者是个擅长营造画面的人,而且这些画面多为电影式的,它们引导读者去构图、静观、省思。许多场景仿佛是在电影中看到,在书本中读到,然后再和作者一起,在现实的场景中去勾画和校对那些零零碎碎的记忆和印象。
电影也好,书本也好,都是作者体验自然的媒介。很大程度上,博物学家们总是带着一层“深度滤镜”去观看自然,自然对象永远都是和文学/艺术对象交织、重叠的,而媒介本身也预设一种敏感、克制、诗意的接触模式。在书中,作者多次把这种“观看”比作“阅读”:“可以说我对自然的热爱是经由文学、经由本能而来……”;“带着纯粹的旁观者的眼光,以及全然的接纳、吸收的状态,都能让步行变成一种精神上的休息、很放松的阅读。”;“仰视天空,对于我来说,既是观察,也是一种阅读。这个世界于我,到处都充满着阅读理解,我阅读树木,阅读花朵,阅读鸟,现在又开始阅读天空……”;“心里忽然浮现诺曼·麦克林恩的话:阅读河水。”
于是,当作者伏案去创作自己的文学幻象时,所构造的画面自然而然充满了“滤镜”的特点,充满了“小津安二郎式”的电影感:读者成为一个仰视的静物,而自然物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意义场所。而作者,一个浑身都是教养的行者,正是在这样的画面中展开她的阅读、她的添写。在山野和在书房,未必有截然的区别。
“大自然重复自身”
大自然重复自身,文学也是。
因此,无论是观察/记录前者,还是阅读/书写后者,都需要无限的耐心、对细节的迷恋,以及对缓慢的信仰,这些在这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今年的四季,在点点滴滴中追忆上一个四季;此刻阅读的那本书,呼应着曾经令人心动的只言片语。博物作家们描绘自然,同时也在评述前人的描写。“约翰·巴勒斯的那只林蛙到底有没有眨过眼睛”这一篇直指自然文学家之间时空或重合或交错的对话,“云曾经来过的地方”借由“云”勾连起好几个西方精神谱系上的诗人、哲学家、气象学家和画家。“重复”的意义,在于为自己的誊写留下空间,也在于邀请新的目光和笔触加入。
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在“重复”中,新的东西持续不断地涌现。作者不知疲倦地赏树、拍花、拾果、观鸟、养鱼、听虫、追雨、看云,因为关于任何一个微小事物的认知都没有尽头,“你需要不断地努力,才能看到自己眼前的事物”。新的认识为旧景添加了自我的独特印记,正如作者见过银喉长尾山雀一家之后,看到的“无数个黄昏的山色中最特别的一个。”而保留着自我与自然接触的温度回过头去阅读,总能读出不一样的意味。
在自然和文学中,创造依托于重复,作者总惦念着老路。“想想我们的生活,就是依靠着许多固定不变、可以预见的事物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定感。”
“无论漫步何处,最后必定是大体未变地回家”
在此书中,作者提到的“精神伙伴”在空间上都离她比较遥远,大多是西方的生物学家、诗人和艺术家。这一点很有趣,它除了说明对自然的热爱是超越国界、语言、文化的,或许也说明激发现代读书人去倾听自然的,并非主要来自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
但无论如何,它热衷描绘的那个对象,具有不可消解的本土性;对于在其中生活过的人,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就我个人而言,这本书让我回忆起我学习、生活了七年的北京——那几个我游荡了不知道多少遍的城市公园,它们的春夏秋冬,还有我在其间浪费的情愫和人生,以及我假想自己与那片土地上的生灵曾共享过的瞬间。当我的某些过往在别人笔下优雅地复现时,回忆仿佛真的更美好了。但与作者的耐心和细心相比,我觉得自己又似乎从未在那里真正生活过。
从各方面看,此书都是一本出色的“译作”。它为中国的读者介绍了许多国外优秀的博物作品,为南方的朋友描绘了北方四季分明的盛景,为北方的旅居者解读了城市乡野最细微的自然变化。但最终,文学是异乡,归属在自然。而自然,是个体生活世界的实然——无论赋予它多少文学想象,都要以脚下土地的坚实性为依托、为牵制,才不会迷失于虚无。这不是劝诫读书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老生常谈,而是人类精神向自己肉身性、自然性的坦然接纳和平和皈依。正如作者在这本书中向我们生动地、真诚地展现的一切:“我们在本源上,就是这样跟自然紧紧相连在一起的呀。”
“在我的房间里,世界超出我的理解”
那些读书人为何漫步林间?
我想,阅读《北方有棵树》,能为这个问题提供相当有趣的解答和遐想。在作者笔下,林间有人情的善意、有荒野的自由、有独处的宁静,有不同物种组成的一个小小共同体、一片独特风景带给人类这个物种的心灵慰藉。林间是另一个书房,提供给读书人可靠的精神食粮。林间的变与不变那样简单而又无限复杂,是灵感迸发的场所。最后,一棵树也好,一片林也好,它实实在在的存在,有时候能超越浩瀚书卷和超载信息带给每个人的困惑、焦虑和失落,带领我们重建天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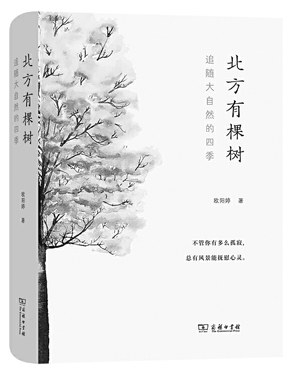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