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暂坐》写了啥?以我看,写了一个茶庄。可这个茶庄并不简单,茶庄里有一堆女子,这堆女子是在都市里以自己女性的生存技巧来活的,她们每个人都是一根拉动都市的神经,这个茶庄就成了神经中枢。只写女人,这在贾平凹创作谱系里还是第一次。
茶庄老板是海若,海若也是这堆女子的核心。作品从俄罗斯美女伊娃来西京开始,最后结尾是茶庄老板海若为首的一堆女子零散了,伊娃离开西京。从伊娃来到伊娃离开,这是一个圈线,这线上可以挂许许多多的故事和人物。但这还不是本部作品的结构所在。这部作品的结构似乎构结了两个球体,以海若为核心的球体,像极了太阳系,她的周围聚结了九个姐妹。而作为西京大名人的作家羿光则是一个孤球,是海若这个球体的光芒,没有他,海若球体依然运转,但海若她们将黯然失色。
作品里的西京始终被扣着雾霾。雾霾是说不清的阴沉,更是都市人道不明的命之运数和生活浊度。这显然是作者一个隐晦至极的寓喻罢了。
我在阅读贾平凹作品的时候,从不在意他说了什么故事,而更在意他是如何叙述的,如何结构的。在这部《暂坐》里,我要寻究的技巧到底在哪里,阅读完后回思,竟觉得没有技巧。就是那种生活化的叙述,完全没有了一些作家那种刻意把技巧挂在手腕上的操作。没有痕迹,就是大技。和《废都》比,我更喜欢这部作品的清俏和窄小。它没有像《山本》那样的雄阔气势,而把视觉仅仅放在都市里几个店铺酒吧里弄里游弋,然这种游弋反把都市的肌理看了个透。这不是一般手笔可及的。在陕西,窄细着为文,是相悖了陕西文坛多数认知的,是绝对要被讥为视野低放的,这种鉴识是和受柳青路遥陈忠实等构筑并遗后的博大传统驯养出来的,他们就是要大,大结构大故事大人物,在读者心里再落下的大阅读。但在我看来,大场子里的表演,更具功力的不是几十人几百人的挥臂撸拳,而是一招一式那种细微里的扎实拳脚。就像是芭蕾女子的脚尖旋转。我看中的是这。从近年的阅读里(原谅我阅读之寡浅),我以为像这样精微到用一爿店而把都市交织得飞升起来的作品还不曾见。这不得不说是贾平凹的又一肘外功夫。屋里是黑的,从门缝进来的光就格外亮,看出去也格外有景致。有的人看锦绣之体,我则要看毛孔的光润。
这部作品里很少提及男人,少有男人形象的作品,当然爱情就困乏,果然作品里几乎没有爱情的蘸笔。只有夏自花那个“野花”般的爱情,其男人涕泪交流的举动反而辣蛰了我心。作品里基本没有性描写,只是羿光和伊娃的一次,那还是模糊的一个居夜,整个作品里干净得让人不忍。但这并不是说都市就干净洁整得让人可以随便坐放。在干净里更觉得都市的纷繁动荡和暗流涌浊。
我要说我对作品的另一个重要感受了。那就是《暂坐》的雅韵和六彩。
贾氏语言在几十年的文学流域里已经成为标签荡漾开来,这不是他一日之功,而是在渤海般的古学基础上渐进而来。他小说语言的那种淋漓、琐碎和口语化,又绸丝般的诗意烘托,把汉语的五谷清香蒸腾出来了,以别样的姿态有着更温和的又诡谲的穿透力。语言的魅力使贾平凹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阈里成为极可贵的一方妩媚。
《暂坐》始终氤氲在古文化的气氛里,尤其是把中国佛教道教文化滴渗下来的东西化为文学的滋养,这在文学作品里是鲜见的。贾平凹多年来浸淫在宗教里,把自己的身心和宗教融为一体,这不是某些人所诋毁的那样,说贾平凹在故弄玄虚里炫玉贾石而粗作,在我看来,他是在宗教里得到某种神助,使自己与宗教之元音接了轨,他想脱离宗教的气流都很难了。一座终南山和许多他淘来的古董,围剿了他,使他在一步步朝一个异于或宜于他身心旨向的地方而去。作品里处处诗语,处处禅意。早年他写诗的经历给他在晚年的小说普及了更广大的诗界。一部皇皇大作,被推拨不开的古境诗意所羁迷,我看到的是明清笔记和冯梦龙吴敬梓等对贾平凹的雕琢到了如此不可偏转的程度,而恰恰不是《红楼梦》和《水浒》。
一场花事后,花叶落尽,这是作品的结局,也是我们为她们,那堆女子命运揣测悬念的时候。使作品余音绕梁。一部作品如此能把“韵”和“彩”集结于一体,真不多见。为什么说是“雅韵”呢?它契合了古之韵,文中多次引用老庄佛经等文句,使阅者自然时时回穿着古往。
那“六彩”又作如何解呢?一彩显然不能概括这部作品,我想二彩呢,也不行,四彩五彩又如何?还是不能,除过一堆彩丽女子的命运沉浮,斑斓里见粼光。六彩就是多彩之意。
话完了。打住。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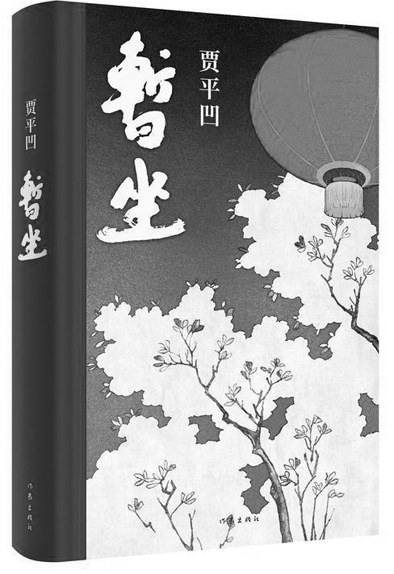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