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容将这几年业余写成的文字结集出版,定名为《此心安处》。在她笔下,当下的生活与记忆里的世界互为参照,那些最具价值的人生经历,从记忆深处复活。可以说,是对故乡的思念激活了她的创作欲望。
她饱含感恩之情,书写着故乡那片山水中的人和事,赞美养育她的那片土地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些文字全部串联到一起,大别山南、长江北岸那片丘陵和平原上曾经过往的人与生活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不仅是对故乡生活的礼赞,更是一首韵味悠长的有关青春的抒情诗。
海容写了一些故乡的原风景,但这些只是生活的背景,她更关心的是父老乡亲和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海容说到自己的写作目的:确立自我价值并给家族留下史料。在辗转多地并不断变换工作单位和岗位的过程中,写作成了她倾诉自我情感及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方式,迁徙让海容以历史眼光审视个人经验的价值,为已经凝固为历史的大时代提供别具一格的个人叙事,通过细节选择和剪裁,复活了当年某些历史场景。
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则隐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她想告诉那些关爱自己的亲朋好友,不管在什么岗位,自己都会努力做好,因为自己是大别山的女儿,大别山培养了她坚忍不拔、热爱生活的禀赋。
历史意识和自我价值的追寻,使得海容的作品,看似行云流水,甚至絮絮叨叨,但却建构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世界。这个世界里,亲情让她感受乡村生活岁月的艰辛而美好,父母的培育、哥哥姐姐对她的关心呵护,点点滴滴,难以忘怀。求学路上那些对自己有影响的老师和同学,让她心生感激。
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的经历,总是和大别山的民情风俗粘连在一起,对于拥有相似生活经历和背景的人们,阅读海容的文字有一种很强的代入感,仿佛自己穿越时空隧道,再次体验成长岁月里的生活与场景,同曾经青涩的自我进行一次心灵的对话。
海容的父亲家庭成分不好,在那个以成分定人品、定工作的年代,他很幸运地成为城里人,工作上,勤勤恳恳,廉洁奉公,对家有责任感,对孩子严厉,像大别山南的许多父亲一样,他们爱子女,却缺乏表达感情的方式,以至于和孩子的关系并不融洽,恰恰是这种不融洽的方式,彰显父爱的独特魅力。海容写出了父亲的严厉甚至粗暴,也写出自己对父爱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
计划经济时代,海容的父亲是公家人,母亲则在乡下种田,当时这叫“半边户”,可以想象,既要抚养孩子,又要参加生产劳动的母亲,是多么不容易。海容写出了父母文化层次、生活环境及个性的差异,更写出了父母的相互包容理解和彼此呵护。他们可能没有绵绵情话,但相濡以沫的夫妻情,让人感动。
母亲去世前,刚强的父亲为自己的女人写了一首诗,将内疚、感恩和对婚姻生活的总结融入其中:“今生难补歉疚意,来世再续鱼水情。风雨同舟已到老,奈何桥畔君先行。”
这也是我们大别山地区千千万万父母的缩影,他们在艰难中相互扶助,抚养儿女,生命进入最后的黄昏时,不说自己给予对方多少,而是内疚自己给予对方太少。这就是父辈的爱情。
海容的叙述语言温婉平淡。精心挑选的一些字、词,蕴含着独到的地域文化元素,只有浸淫其中的人,才能体会其言语后面的全部语义。而当你知道这个词的内涵,就禁不住发出会心的微笑。“超支坨子”就属于那个远去时代的语词。没有在大别山农村生活过,没有在生产队挣过工分的人,大概无法理会其中的意义,它隐含了长辈对生活负担的戏谑、对孩子的怜爱,还有愿望得不到满足的自我嘲笑和安慰。
海容文笔细腻,一些细小的事情经过她的叙述也变得灵动起来,饶有趣味,而一些我们熟悉的人,经过她三言两语地勾勒,精神气质、性格特征栩栩如生。
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还是师生情,海容的文字都和故乡联系在一起。正是泥土芬芳的故乡叙事,让海容领略到思考的魅力、文字的价值、情感的力量。写作使她获得自我实现与满足,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因为用情太深,她甚至过滤掉了记忆中灰暗的色彩,即便写到生活的困境,也是积极和乐观,我以为作家以这样的姿态切入生活无可厚非,因为经历过的苦难已经内化为个体奋斗的精神力量,成为克服困难的垫脚石。
可以这样说,故乡赐予了海容成长岁月的宝贵财富。这似乎验证了作家余华对故乡的体验:“只有离开了你最熟悉的地方,你再回来,才知道真正的财富在哪里”。
我们这代人,曾经怀揣梦想,把远离故乡作为目标,仿佛只有走得更远,才能飞得更高,才能确证自己人生的成功,然而等到岁月堆积到一定的年纪,无论我们身处何处,故乡永远被安放在心灵最柔软的地方,成为无法割舍、永不忘却的心灵家园。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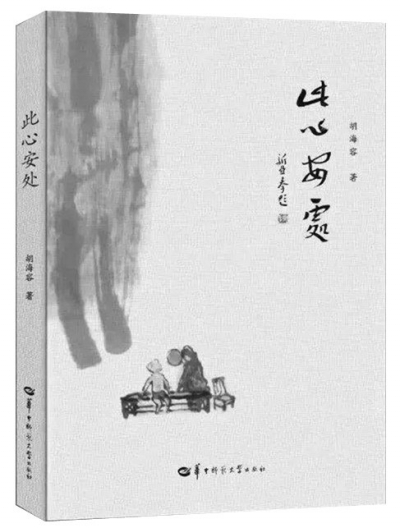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