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木圣经》中这种多视角的第一人称讲述与《罗生门》不同,后者在故事的推进层面来看,是纵深式的,围绕一件事不断纵向内切;而前者则是五位女性以各自的讲述将故事横向推进,使得故事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发展。这样的写法很考验作家,她不仅要分身为五个不同性格、年龄的讲述者,还要依照外部环境的变化为这五个人选定符合逻辑的抉择。
向来不太爱读外国文学作品,即便写得再好,也总觉得隔了一层。那种感觉就像摘掉眼镜看星星,虽见漫天闪耀,但看不清具体。如果再碰上个不合格的翻译,星空之下又蒙一层雾霾。这本《毒木圣经》足足有576页,共47万字,初拿到时,觉得它绝对超出了我对外国作品阅读的极限,没打算能坚持到底。翻开书,硬着头皮读完前十几页,然后慢慢顺畅起来,花了两天时间顺利读完。
《毒木圣经》封面极其花哨,像是特意选取了符合非洲气质的明艳色调,但内封非常素雅,像是笔记本的封皮。这本40多万字的小说大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美国牧师拿单自认为是上帝最忠实的牧者,于是他带着妻子和四个未成年的女儿踏上了非洲大地,来到比属刚果一个名叫基兰加的村子,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拿单信仰坚贞,但妻子和女儿并不如此。他的妻子奥莉安娜并不认同丈夫的事业,但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她还是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基兰加照料一家生活。
大女儿蕾切尔是个娇滴滴的美国少女,梦想是成为选美小姐。小蕾切尔一岁的双胞胎女孩莉娅和艾达性格迥异,莉娅在初到基兰加时总是跟在父亲身边,试图得到他的赞赏;艾达因在母亲腹中时发育不良,造成先天性偏瘫,只愿做一个沉默寡言的思考者。最小的女儿露丝·梅只有5岁,每一处能玩耍的地方都是她的天堂,无论是美国还是刚果。生活对这个家庭的压迫不止在于物质方面,刚愎自用的拿单作为这个家庭的主人和唯一的男性,他的光芒或者说阴影时刻笼罩着每一个人。但颇为讽刺的是,西方人给刚果人带来了“耶稣项目”和“选举项目”,基兰加酋长塔塔·恩杜却用“选举项目”将“耶稣项目”逐出村子。基兰加村民对“选举项目”产生了好感,在一次投票中,牧师家的二女儿莉娅被同意可以跟随男人们一起去打猎,这件事触怒了基兰加巫医塔塔·库伏度,他恐吓这种颠倒自然之道的做法会让人蒙难……
我的梗概不及原书的百分之一精彩,因为《毒木圣经》不仅有一个好的故事,还配备了好故事的讲述方式。小说就是故事的讲述方式,同一个故事有无数种不同的讲述方式,优秀的小说家总能找到最恰当的一种。
从结构来看,《毒木圣经》共分为创世记、启示录、士师记、神与蛇、出埃及记、三童之歌、树之眼七个部分。前五个部分都先由母亲奥莉安娜一段回忆性讲述起头,然后由女儿们轮番充当第一人称叙事者。在前五部分中,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小标题跟在母亲奥莉安娜的讲述之后:与创世记相对应的是“我们所携之物”,与启示录相对应的是“我们所学之事”,与士师记相对应的是“我们未知之事”,与神与蛇相对应的是“我们所失之物”,与出埃及记相对应的是“我们携走之物”。这其中的“我们”,指的就是牧师家的四个女儿,每一个小标题都扣住了那一部分主要讲述内容,也顺理成章的开启了多视角第一人称的独特叙事方式。虽然对《圣经》了解不多,很难体味出作者在标题和内容安排上的所有意味,但仍能感受到这部大部头作品精巧的结构排布。
如果要挑选出《毒木圣经》在小说层面最独到之处,我认为是构成整个故事的五位女性各自的第一人称讲述。《毒木圣经》中这种多视角的第一人称讲述与《罗生门》不同,后者在故事的推进层面来看,是纵深式的,围绕一件事不断纵向内切;而前者则是五位女性以各自的讲述将故事横向推进,使得故事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发展。这样的写法很考验作家,她不仅要分身为五个不同性格、年龄的讲述者,还要依照外部环境的变化为这五个人选定符合逻辑的抉择。人物随着年龄和境遇不断变化着自身性格,就像莉娅,她起初是上帝和父亲的信徒,但她的信仰又不是那样单纯和笃定,或者说,她更想得到的是父亲的赞赏。随着心智的成长和家庭状况的变化,莉娅慢慢变成父亲的反对者,她离开父亲但没有离开非洲,她用与父亲不同的方式来改变这片黑色的土地。
如果要说这部小说的不足,我认为是男性视角的缺失。不知作者芭芭拉·金索沃是否有意为之,文中处处都是女性对男性——上帝、拿单以及各路政客——的指控,却没有男性为自己发出声音。文中着墨最多的男性人物是莉娅的丈夫阿纳托尔,但他更多的是为表现莉娅而设定,作为一个功能性人物而存在。没有看过芭芭拉·金索沃其他作品,不知她是否真的不善于描写男性,但如果从追求更高的作品完成度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应该增加一重男性视角。比如,让牧师拿单也有自白的机会,或者,把双胞胎改换成龙凤胎,将偏瘫女儿艾达换成一个男孩,看这个男孩如何对待自己的父亲,如何对待母亲和姐妹,如何对待非洲和美国。如果这样,故事就多了一个视角,增加了一重声部,更显立体性和丰富性。
故事的独特讲述方式带来一个问题——谁是真正的主角?五位女性讲述者都是从其个人角度展开叙事,显然每一个都不能作为整个故事的主角。那么,最有可能作为主角的就是牧师拿单。但从文本来看,全书自四百页“出埃及记”开始就鲜有提到父亲的故事。作为牧师的父亲隐去,但另一个父亲却时刻在场,他就是——上帝。
所以我认为,上帝才是整个故事的主角。上帝在文本中无时、无处不在。母亲奥莉安娜不是上帝的信徒,蕾切尔心心念念的只是西方物质文明,莉娅成长为上帝的背叛者,艾达从一开始就在沉默中反抗,而露丝·梅还是未经过洗礼幼童。对上帝旨意的反抗不止存在于这个家庭,也不止存在于基兰加,而是更广阔非洲,甚至整个非西方国家。一位来自比利时的医生在与拿单争论时曾说:“我们比利时人在橡胶种植园里把他们当奴隶,割断他们的手。现在,你们美国人又在矿井里让他们当奴隶,直到他们把自己的手割断。而你,朋友,还一门心思的做着这份工作,想让他们说阿门。”
文明成为一条类似食物链的等级结构,信仰上帝的白人来到这片蛮荒之地——黑色非洲,试图用自己的文明将其启蒙。他们带来“选举项目”和“耶稣项目”,却又为自己的利益将刚果人自己选出的民族英雄杀害,同样富有戏剧性的是,基兰加人用“选举项目”驱逐了“耶稣项目”。拿单牧师的结局颇具隐喻性,作为上帝的使者,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言人,他被烧死在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塔楼之上,神权、霸权、夫权、父权,一火炬之。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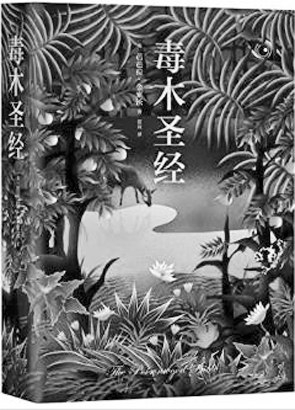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