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喜闻乐见的书,不会是拒人千里之外的高头讲章,或是面目可憎的心灵鸡汤,而是活泼泼的有趣有益之书。所谓活泼泼的,就不能板起面孔说教;有趣,强调的是可读性,而不是斧凿痕迹历历可见的匠人之作;有益,则是可以引发读者思考、带来启迪。
聂友军主编的《取醇集:日本五山文学研究》,一部由青年教师与研究生读书会成果汇编而成的论文集,就是这样一本活泼泼的有趣有益之书。《取醇集》既有宏观鸟瞰式的整体总论,也有单篇深入精微的文本分析解读,所收文章大都有趣味、有见地,引人入胜。比如单以论题所及,就包括五山文学中的杜甫骑驴、梅妻鹤子、杨贵妃、牡丹花;有关西湖的诗文、西湖图、西湖意象;禅僧的思归、交游与归国路线考;东亚视域内的国交文书;禅僧身份与儒学教养的一体两面、相反相成,等等。
在内容方面,《取醇集》通过细密地研读日本五山文学,一方面梳理日本汉诗文与禅宗的关系,分析文学的承传、赓续及社会功用;另一方面整合内在与外在视角,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世时期的日本;最终将落脚点落实到探究古代中国文化到对日本文化建设所起的推动与反拨作用。
从《取醇集》所收的多篇论文可以看出,“五山文学读书会”较为注重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训练,求真、求实、注重材料的原典性的意识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但五山文学毕竟隶属于文学学科,所以文学研究的方法亦得到着力彰显,那就是在求真的前提下,不仅明了“其然”,而且勉力探求“其所以然”。以聂友军的《道出文字言说,舍疵取醇》一文为例,较为清晰地体现出“是什么”(what)——“怎么样”(how)——“为什么”(why)的三个层面。尽管在原因探析方面难以做到尽善尽美,但毕竟在方法论层面上超迈前贤,跨出了坚实的一步。
治学方面,拒绝跟风,强调脚踏实地;并有意识地汇通中外文化思想。聂友军在“前言”中提到:“做学问最忌跟风、赶时髦,人人趋之若鹜的显学极易变为俗学。”(第2页)在“编后记”中说:“近代以来在人文学领域能成一家之言的方家大多既具备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对特定的外来思想文化有学理上的把握。”(第192页)并称《取醇集》是“着意加强上述两方面修养的一个尝试”(第192页)。
《取醇集》的多位著者倡扬辩证地看待中国文化、外国文化以及文化的交流、回还与往复。他们用一种历史研究极为珍视的客观态度和笔法,不虚美,不隐恶,真实并比较具体周到地叙述中国文化如何为日本五山禅僧所识、所用。他们从观念上超越了“影响-接受”与“冲击-反应”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突出五山禅僧对外来文化的选择、过滤、吸纳、重组与改造的主观能动性。
当年萧统在为《陶渊明集》作序时曾不无遗憾地指出:“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落实到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该论断仍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对历史资料的梳理与解读过程中丝毫不考虑其当下意义,不从中借鉴并获得教益,这种梳理与解读的价值必然大打折扣。如此说并不意味着将一切历史都视作当代史,或者牵强地硬性从历史资料中生发出对当代的启示。
同理,对外国资料的占有与分析,如果没有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的清醒的主体意识,那么基本可以断言相关研究难以做出一流的成就。比如用英国学界通行的理念与方法研究莎士比亚,或者与日本学者取相同的路径研究本居宣长,单就语言层面而论,我们中国学者就很难超越一般的英国学者抑或日本学者。这时我们作为中国学者的知识背景成为不可多得的优势,我们必然会从中国人的关切入手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与研究对象拉开适当的距离,有助于客观审视,在此基础上再加以并细密的解读,俾可发现对象国学者司空见惯而不知设问、存疑的地方,深入探究下去,造就对象国学者做不出的成果也就成为可能。从自身的知识背景与问题意识出发,充分发挥主体性,这正是比较文学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比较得以顺畅开展的有效路径。
正如书名所蕴含的“舍疵取醇”所示,“取醇”首先是一种姿态,既避免自视甚高、无视他者的虚无主义,也避免自我否定、迷信外国的自卑主义;还应成为一种方法,对研究对象、外来理论尽量保持平视姿态,以客观公允为旨归,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更进而上升为一种理念,既充分揭示对象丰富复杂的面貌,又着眼于中国人文学术的整合重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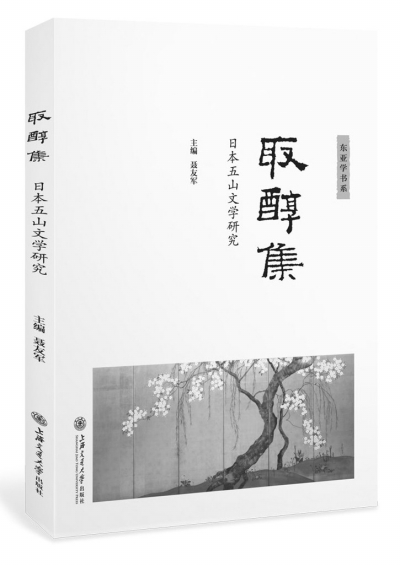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