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的科幻作家夏笳在声名显赫的《Nature》上发表了一篇英文科幻小说,引发了国内媒体的一番报道,许多人也因此得知,原来这本备受许多自然科学工作者仰慕的杂志也会刊发科幻小说。其实,早在上世纪末,《Nature》就设置了“未来”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科幻短文,受到始料不及的欢迎,许多顶尖的科幻作家和严肃的科学工作者都曾在此发表这一类虚构故事。后来,专栏的主持人亨利·吉从中挑选了100篇,编为Future from Nature一书,并由著名的科幻图书出版商Tor出版。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这本选集的中译本《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让我们得以一窥究竟。
亨利·吉显然是带着几分骄傲来编辑此书的,他将《Nature》与科幻的渊源追溯到有“科幻界的莎士比亚”之誉的H·G·威尔斯,并希望通过“未来”专栏向人们展示这本以刊登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成果著称的“严肃的出版刊物”,永远乐于做出一些新的尝试,并保有一种“纯粹为了好玩”而勇于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不过,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穆蕴秋和江晓原两位老师,编译此书却另有目的。在他们看来,科学早已不是一位纯真的少女,而是和商业资本密切结合,科学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弊端需要批判和反省,因此有必要破除许多人对科学的盲目崇拜,《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即表明“反思科学”已成为科幻创作主流。同时他们还认为,集中作品作为小说,水平也不过如此,是一种“华贵下的平庸”。他们在此书的导读中同样提到了威尔斯,不过却是为了说明,这位在《Nature》上发表了26篇文章的文化巨匠,并不能凭此被英国皇家学会接纳为会员,所以这份许多人眼中“世界顶级科学杂志”,其实是一本“普通的大众科普读物”。
为了展示“平庸”而译介作品,从出版的角度来说,多少显得“另类”。不过,我并非科学行业的从业者,无力对《Nature》的光环做出评判。事实上,这本书带给我的,主要是一种焦虑:我虽然是一个从科幻迷成长起来的科幻小说作者,并在大学时学过一点自然科学的皮毛知识,但面对这本小说集中的一些作品,却总是看不懂,这让我深感惶恐。
由于专栏篇幅规定,这些作品都不超过950个英文单词,因此不可能提供充裕的情节容量,谈不上多少人物塑造和戏剧冲突,基本都以一个技术幻想的概念为前提,讲述一个特定的事件,比如一个装载了软件而怀着浓烈爱意飞向恐怖分子的导弹,或以量子纠缠理论为依据的人与万物之间的心灵感应,甚至以机器人口吻撰写的、或许只有计算机高手才能欣赏其中笑点的小说,等等。它们和各种科普文章一同呈现给《Nature》的读者,对他们而言,小说中的种种科技名词大概不构成什么理解的困难,但当这些作品被抽离出它原本的语境,在另一种语言中呈现给一般读者时,即便有译者对个别概念的补充解释,仍难免显得坚硬和生涩。如果小说中描绘的情景有一天变成现实,那就已经不是我喜不喜欢这样的未来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我甚至可能根本理解不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换言之,我为自己的无知而焦虑,害怕无法进入“未来”。
也正是在最近,在一所大学里,一群中国科幻作家受邀参加了一次“后人类”工作坊的会议。“后人类”是近年来很热门的科技和科幻议题,这就是说,基因改造、人机合并等正逐渐从科学幻想走进我们的现实生活,人类的定义正面临挑战,这也是《Nature》上科幻小说偏爱的主题。于是,我不免又联想到在几年前才初次接触到的关于人类未来的“奇点”理论:由于科技以指数级速度进步,人类社会终将进入一个奇点时刻,它仿如“黑洞”,超越我们现有的认知,以至于目前对它的任何猜测都可能是无效的。据说,这件事甚至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实现。当时,我并没有很当真,毕竟,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地方仍停留于近乎前现代的阶段。
后来,奇点即将来临的说法似乎越来越多,但因为要撰写学位论文,我只得把自己浸泡在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中,也由此产生了一个模糊的感觉:其实“奇点”时刻曾经降临过。当李鸿章认定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遭遇带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不正说明那是一个旧的社会形态和思想意识剧烈崩解的时刻吗?作为“公理”被接受的进化论、物竞天择的种族竞争压力、实证主义方法论、感知时间和空间的新方式、科技进步所允诺的光明前景、可供人类征服的地外空间……凡此种种,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为近代中国带来了种种不幸、先进发明和全新的宇宙图景,重塑了中国人做梦的方式和自我理解的方式。在被飞驰的进化之轮碾压的焦虑中,彼时的国人对于何为“人类”,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人类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有了全新的理解,并初次尝试用小说来描绘科学为人类带来的巨变。和《Nature》上的科幻作者一样,晚清的小说家也试图借助他们从书报上听说的各种理论学说来勾勒未来,因此,小说中同样汇聚了会让当时的许多中国读者感到摸不着头脑的新鲜字眼,什么“脑气筋(神经)”、“阿巽(臭氧)”、“以太”、“脑电”、“拉的幼模(镭)”、“动物磁气”等等,令人目不暇接。不同的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他们普遍缺乏系统的科学训练,因而对自己笔下的科技概念往往也只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而已,难免放纵奇想,写出些离奇古怪的事情。作为一名后世的研究者,我面对这些曾经很前卫的故事时,常有哭笑不得之感,并难免有几分难以摆脱又无甚道理的优越感。然而,《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的出现,让这种优越感荡然无存,也令我对一个多世纪前的先贤面对西洋科技时所饱受的刺激有了更为感同身受的体会。和他们担心中国人不能成为合格的人类一样,身为一名小说作者、文学研究者和普通的人类一员,我也在《Nature》上的这些最新科幻小说面前诚惶诚恐,感到“后人类”的奇点时刻正飞速逼近时的身手无措。这种感觉并非我独有,科幻作家韩松也认为这些作品“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写法,或者风格,就好像是未来人写的,坦率来说,有的要看第二遍,才能抓住里面的精妙味道。我读的时候,好像李白来到二十世纪,读我们写的文章。这是真正的科幻。”
实际上,晚清用小说来普及科学的努力并不成功,到了民国,重要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基本上放弃了这样的念头。小说这样的形式,究竟是否宜于宣扬科学?这是个贯穿二十世纪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问题,这里无暇展开。其实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有句话说的好:人们都能预想到汽车的发明,但只有科幻作家去思考堵车的问题。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上,刘慈欣引用了这个说法,并强调科幻文学更擅长的其实也许是表现科技概念一旦成真后的社会问题和美学感受。然而,在今天,3D电影、游戏、虚拟现实技术等新的媒介方式,在表现超越当下的科幻世界观时,其实比传统的书面文字书写有着太多的优势。比如说,这本小说集中的《迪昂·哈勃之痛》,讲述了记忆可以拷贝之后,人可以有多个克隆体分身。如果从概念表现上看,与这篇小说差不多同时问世的科幻电视剧《太空堡垒卡拉狄加》可能更胜一筹:机器人复制体死亡后,记忆可以上传到另一个躯体中,死亡的经验因此成为一种痛苦的学习,这要比900个单词左右的短文更能冲击读者的认知和情感,而在地铁上用一个移动设备观赏这样的电视剧,并不比阅读一篇让人意犹未尽的小说更费神费力。换言之,当科幻小说构想出的神奇技术成真并改变我们的现实生活时,这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蓬勃发展过的文学样式,自身却面临着衰落的危机——刘慈欣在《三体》大获成功后的几年来很少写作小说而更多投身影视、游戏等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今天,一个科幻小说作者,究竟能指望自己为读者带来什么呢?
更进一步,当我们的身体植入电子设备,机器则越来越聪明甚至可以创作小说时,人之为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奇点之后的世界,究竟是一首人类终结的悲伤挽歌,还是一曲后人类启程的欢乐颂?未来的(后)人类将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它又将如何描绘(后)人类的生活?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将成为过时的古董,还是激活出“后人文主义”一类的新能量?文学研究又如何应对这些议题,人文学者将何去何从?在人类社会生活发生着巨变的当下,如果不及时学习新事物,我们是否会被关在新时代的门外?对我而言,《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出现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作为小说的思想价值或艺术价值,而在于它挑战了我在汲取科技新知和理解当下世界方面的惰性,迫使我思考这些令人迷惑的问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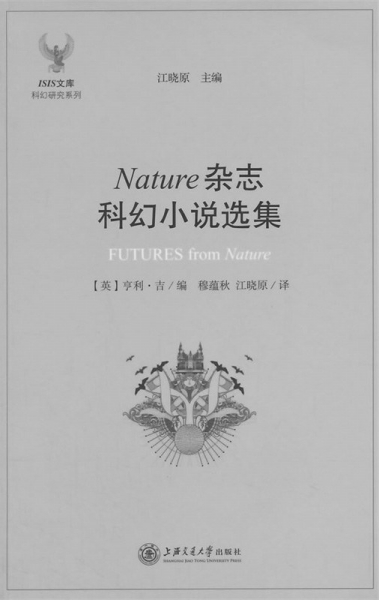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