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准确描述和剖析巴金的一生,在曲折多变的中国现代文坛背景上评价他的文学贡献,对传记作者来说是一大难题。
一个多月前,老友陈丹晨冒着酷暑来到舍下,把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全传》(上下册)赠送给我。当我从他手中接过这部沉甸甸的新著,并得悉我是第一个得到赠书的人时,不假思索地对他说:“您写了那么多书,包括文学评论和散文结集,出了就出了,只有这本泣血之作才是您的代表作,是可以传世的!”这不是虚于应付,这是我的由衷之言。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据我了解,他对巴金的研究,起始于新时期之始,迄今已有30多年了,在如此漫长的文字生涯中,他不畏艰难,锲而不舍,不断地冲击思想禁锢,也不断地解放自我、超越自我,在这部书里倾注了他从青年到老年的才华和智慧,付出了大半生的辛劳。他的第一个成果《巴金评传》问世于1981年,是我国出版的第一套“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花山文艺出版社)中的第一本书,而他对巴金的研究并未因“评传”的出版而就此止步,继而又撰著了《巴金的梦——巴金的前半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2月)、《天堂·炼狱·人间——〈巴金的梦〉续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2月)。如今这部长达799页的《巴金全传》,乃是在这三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最终成果。我怎么能不为他的这部煌煌巨著高兴呢?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不仅艺术地概括了中国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及其矛盾,而且曾给万千步入社会和走向革命的青年读者们以思想的启迪和审美的陶冶,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巴金就是这些文坛巨匠之一,尽管他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诚然,巴金是一位有着丰富复杂的生活史、奋斗史、心灵史、信仰史而又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作家,要准确地描述和剖析他的一生,在曲折多变的中国现代文坛背景上评价他的文学贡献,对传记作者来说,毋庸讳言,是一大难题。在我读完了全书后,我愿意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读后感:“丹晨,您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巴金!您实现了‘尽其所能地向读者介绍一个真实准确的巴老的形象和心灵’的原旨!”
传记写作,在我们的文学界,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很不发达。个中原因固多,但笔者以为,最主要的是文艺指导思想上的“左”和文艺政策上的“舆论一律”所致,虽然有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出台,但出台未久,就被1957年的反右斗争所打断。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法国文学研究者郑克鲁先生为苏联文学理论家奥勃洛夫耶夫斯基所著《巴尔扎克评传》的中译本写的序言里提出一个问题:“一部作家评传怎样才算具有价值呢?”他的回答是:第一,它要提供较丰富的资料;第二,对作家的某些众说纷纭的问题提出有见地的看法;第三,对作家的创作道路和作品作出比较细致的分析。这三条标准不仅适用于巴尔扎克、甚至托尔斯泰等素有争议的大作家的传记写作,也适用于对巴金这样的作家的生平与创作的评价。
第一,丹晨在《全传》里说:“个人传记是社会历史的组成”。不错,作家传记是建立在作家个人以及与作家相关的社会与文坛史料的基础上的。他始终坚信这一写人与写史的原则,并且贯彻始终。他搜集了尽可能多的有关史料,包括传主的“内心世界”的难得的史料,而且把传主时时放到一定的社会的与文坛的事件与思潮中去写。史料的丰富与完整,细致与准确,落笔处真正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也就是古人所称赞的“信而有征”,因而成为这部传记的重要特点。限于篇幅,恕不举例展开来说了。
第二,上述三条标准中的第二条,显然是与对有争议的巴尔扎克的评价有关的。巴尔扎克是与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并列的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但他的世界观问题却成为在对其评价时最聚讼纷纭的问题之一。对巴金的评价也一样,最绕不过去的,是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研究、阐释和宣传,概括地说,亦即世界观问题。正如《全传》作者所说:“他的大量著译活动,已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一位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在修订新版的《全传》里,作者对巴金各个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作为毫无回避之意,而是作了相当充分的引述和分析,梳理和解读,而在他晚年的思想发展脉络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评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先后到工农兵中去,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总之使他接触和熟悉了过去他并不熟悉的劳动者的生活、人事、伦理和思想,自己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经过十年“文革”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从“炼狱之梦”回到“人间之梦”,以清醒的意识重新认识历史和观察现实,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但“爱人”(泛爱)和“人道主义”等观念,仍然在他的信仰和思想中牢固地占有重要地位。怎样看巴金的信仰和变化?对于这个读者关注的问题,《全传》作者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不必用‘主义’之类僵硬的概念套用到他头上”。诚然,不能用一种“主义”、一种声音来要求所有的作家和所有的作品,即使我们耳熟能详的“党的文学”中也有不同的观点和风格呀。君不见,198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的茶会上作报告,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毅然修改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译文,从此,“党的文学”这个不是法律条文而实则长期起着“舆论一律”作用的名词,被从文学领域里勾销了。
第三,作者在对巴金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所作的交叉叙述中,有重点地对巴金的一些代表作作了的解读和评价。无论是早期的《灭亡》,还是稍后的《激流三部曲》,特别是以对封建家族制度发出猛烈抨击的成功之作、堪为新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的《家》。作者在阐述了以觉慧为代表的反叛性格的、敢于行动人物的时代意义和文学史价值的同时,还把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人物和概念,移植到对巴金作品的分析中来,提出了“中国式的‘多余人’”的概念和论点,分析了《新生》、《激流》(《家》)、《雾》等作品中那些说得多做得少、事情不成时渴望至极、事情成功时又不敢接受的人物的性格。这些典型的塑造,触及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无疑使巴金的小说显示了积极的现实主义的品格和力量。至于巴金晚年以《随想录》为题所写的一系列令人振聋发聩的随笔,无论就其思想的深度而言,还是就其艺术的境界而言,都是富于历史的超越性的作品。萧乾说得好:“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否定自己就意味着超越。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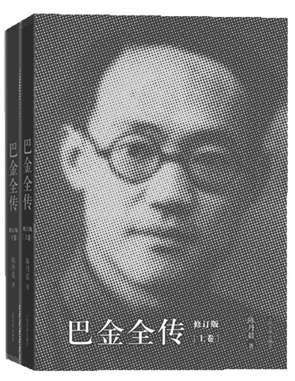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