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女士的这本《青山青史:连雅堂传》,书名取自外祖父连雅堂昔日游杭州西湖的即兴之作:“一春旧梦散如烟,三月桃花扑酒船。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当时正值民国初建,但台湾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连雅堂(连横,1878-1935)从18岁时开始经历异族统治之痛,遂发愿撰著《台湾通史》,以司马迁撰《史记》的格局记录台湾历史。连雅堂一生以笔为剑,办报、创作诗文,致力维护台湾语文与古迹,是一代史家、文学家。
连横的一生,引人注目有几点。一是古典文人的生活方式。他纵情诗酒,组建诗社,是台南地区文学界的中坚力量。他的诗学主张,大体上尊重传统格律,不喜新文学,强调“文以载道”,讲求大格局。《大陆诗章》、《台湾诗乘》是其代表作,在台湾文学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作品。连横的诗作,古风盎然,情感热烈,富于民族意识。对郑成功、孙中山尤为推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诗中至少三次提到祖逖“渡江击楫”的典故,阐明心态。 连横多番游历日本与大陆,眼界开阔。交游的人物中,既有日本和台湾官员,也有王闿运、章太炎、梁启超、张继、胡适等大陆各界名流,还有杨云萍这样的台湾新文学人士。台北上海两地的名媛如王梦痴、张曼君,也与他过从甚密,几近影响他的家庭。
一是积极办报,这点知者甚少。连横以其深厚的旧学功底、开阔的眼界、坚实的人际关系,成为当时台湾报纸竞相延揽的对象。他担任过多家中日文报纸如《台澎日报》、《台南新报》、厦门《鹭江报》、《台湾新闻社》主笔,也参与创办多家报纸杂志如《福建日日新闻》,足迹所到之处皆有创举,甚至远到吉林担任《新吉林报》主笔,又在《吉林时报》创办《边声》报,销售远届西南,可惜只有三个多月便被袁世凯政府勒令关停。连横在台湾新闻史上的地位,实在可以深入关注。
一是学者身份。《台湾通史》是其一生大业。此外,连横利用其报人身份,编辑《台湾诗荟》,搜集台湾本土诗作,整理台湾故事与古迹信息,撰写《台湾漫录》、《台南古迹志》,这些都可与《台湾通史》相互印证。贯穿其中的,是连横对台湾和华夏故国的深情。
最后一方面是他的家庭生活。在著者林文月眼中,连横在那些公共身份之外,是一位孝顺的儿子、称职的丈夫和尽责的父亲,也是有责任心的女婿,更是慈祥而对子孙寄寓厚望的祖父与外祖父。林文月不仅参考了现有的史料、家传、年谱等相关资料,而且还翻阅研究了连雅堂先生所有的诗文著作,并且一一访问了其相关亲属,以及与之交往过的诸多朋友,使得本书所呈现的连雅堂先生远不是一个平面化的偶像,而是一位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
《青山青史》是一部优秀的传记作品,同时又是一部非常可读的散文作品。林文月女士学贯中西,在研究上专精于中古文学,自己长于散文,文字雅驯,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之妙趣。正如评家所谓:“……既述先人行谊而成传记,复又展现他散文书写上通陶谢诗味而自铸新意之古、淡、雅、奇。”
同样是史学家的传记,相比于陈美延、陈小澎、陈流求三姐妹纪念父亲陈寅恪先生的《也同欢乐也同愁》,顾潮女士纪念父亲顾颉刚先生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等书对大时代的痛楚记忆,本书的基调更加“温柔敦厚”,有独特的台湾气息。
本书的瑕疵主要在于两方面: 一是著者并非专业史学学者,方法论较为不足。本书史料丰富,文笔优美,是其胜处。但体例编排失之凌乱,连横的许多事情没有严格的时间或逻辑顺序,有时会重复出现。因为本书篇幅较小,这问题便显得突出。
一是由于与传主的亲缘关系,作者难免“为亲者讳”。我们可以看到家族的一些传说:连横之母梦见有人赠龟于她,随后便生连横,以为吉兆;连横结婚时,其妻沈筱云幻视连横为“脑后结着红辫子的白猿”,还美其为“玉猿”化身。这些都属于一种“加魅”行为,殊不足取。还有对连震东出生时的环境大加修饰,将其出生叙述为“惊天动地”,夸张太过。连横作为学者,谋国难成,谋身有道,尤其为了其子在大陆和台湾的发展,精于盘算,周旋于日本人、国民党和台湾本土势力之间,种种苦心孤诣,便不足为外人道矣。这本情有可原,但也使得这本书的史学价值打了折扣。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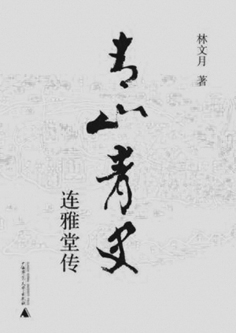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