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和中国,这一课题归属于歌德的世界文学纲领之中。假如不将“歌德在中国”这一相互关系的研究纳入进来,那么歌德的世界文学纲领就会变得片面。自1988年便生活执教于德国、并对中德文化都有深厚造诣的顾正祥先生对“歌德在中国”的研究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前人相关工作的基础上,他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部著作最好地证实了自己。
该部著作中德文对照,精心印制,既适用于德国书市,也适用于中国书市。全书共两大部分。上卷是歌德作品译成中文的篇目,这里包含四个章节:译诗目、散文小说译目、戏剧译目和书信译目。结构完整统一,只是在第四编书信译目中还特别添加了收信人目。全书各栏目按编年史顺序编号排列。每条书目排列顺序为书名、主编者、作者或译者名、出版地、出版社和出版年、丛书名。对于德国读者来说,德文原文标题很是重要,从中可以看出中译的令人惊讶的丰富多彩(比如说译诗目就有265项,散文小说目多达280项,戏剧目达95项,书信目则超过600项)。不仅如此,还显示出翻译的重点,这同时也是中国的歌德接受的重点。《少年维特之烦恼》被一再重译;《浮士德》在翻译中占有突出的位子,而《哀格蒙特》、《塔索》、《伊夫根妮》则被远远抛在后面。令人颇受启发的是,最早汉译发生的时间点。第一批诗歌散文的翻译是在1914年进行的;而戏剧(从浮士德)的最早翻译则发生在1902年;而歌德书信翻译则相对较迟,那是从1949年才开始的。
下卷也给人以深刻的印像,此乃“研究目”,分5个子目,亦即也分门别类列出辞书、专集、合集、文学史和报刊杂志等子目。中国学者对歌德的研究成果除专著外,大多散见于浩如烟海的辞书、教科书、文学史、诗文集以及报刊杂志中。请想想看,为了寻找这些有关的材料资料要花多大的精力!
在我们看来,中国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崛起为现代国家,令人讶异的是,早在1924年,歌德的名字就已出现在中国的文学史中;更令人惊异的是,歌德的名字早在1878年就已出现在《李凤苞使德日记》中。让我们还用数字来说明问题吧:“辞书”一栏共126个条目(始于1926年),“文学史”一栏共124个条目(始于1924年),“合集”一栏共344个条目(始于1878年),“专著”一栏共62个条目(始于1923年),“论文”一栏共528个条目(始于1978年)。尤其是“论文”一栏,呈现出题材的丰富多彩。
对于德国日耳曼学者来说,在浩若烟海的各个类别的辞书中来搜寻歌德的踪迹该是多么不同寻常的壮举。提提那些辞书的名字,比如《中国学生百科全书》、《伦理百科辞典》、《世界文明史年表》、《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文艺·艺术卷)等,歌德在其中都占有耀眼的一席,就令人肃然起敬。在影响我们一生的《名人名言》这一栏目里,歌德也没有缺席。其中的大部分篇幅印证了孔夫子的遗训,也即对人类先贤、世界文化重要人物的敬重。这一点在顾正祥的这部令人惊叹的著作里也得到了展现。
作者将中国对歌德的接受史列出便于查找的框架,将其分成四个阶段:1878-1922,1922-1949,1949-1976,1976直至当代。他曾断言,中国学者对歌德的研究自文革之后无论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其总目录的撰写中也令人印象深刻地证实了这一点。从1919年以来《浮士德》共重译24次,《少年维特之烦恼》则有45种版本。1999年由杨武能编选的14卷本的《歌德文集》共发行了2000套。
顾正祥先生这部著作并非creatio ex nihilo(凭空创作),他为撰写这部长达518页的著作参考了很多书籍资料,他为此不得不长期泡在图书馆里,仅此一点也足以令人敬佩。从其编写的过程可以看出,他掌握了现代系统化的编写方法,分门别类来梳理歌德的作品,其目光之尖锐,工作之辛勤,令人印象深刻。他所提供的不啻是一部歌德关于世界文学互动之构想的生动文献。
(本文原载Goethe-Jahrbuch(歌德年鉴,魏玛)2009年,页334-335。作者约亨·戈尔茨为国际歌德学会会长。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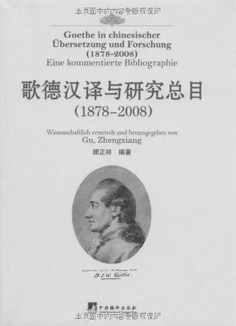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