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之上的文人
1987年1月,三联书店推出辛丰年先生第一本书:《乐迷闲话》,副题为“欧洲古典乐坛侧影”。此书小小巧巧,十万余字,内分十章,含闲话钢琴、闲话小提琴、闲话唱片音乐文化、闲话乐谱,等等。这是很好读的书,叙述清浅生动,充满西方音乐故事。此书印数不低,初版印了一万,当时一般图书印数早已急转直下。严格地说,这是一位大文化人听乐和读书的笔记,它的准确身份,应属“书话”。但时人多看成一般的普及音乐知识的书,未引起特别关注。
真正让人注意这位作者奇特价值的,是他从1989年7月起在《读书》开设的专栏:门外读乐。虽说“门外”,但一下笔,就显得十分专业,而且中西兼通,娓娓而谈,跌宕有致,兴味盎然。第一篇《读曲听心声》,说自己是西乐迷,但在小小的藏书中可以找出三本《梅庵琴谱》,第一本印于六十年前,第二本是1958年重印本,第三本是近年出版的;此外,在“文革”劫难中还损失了两本,所以,这一琴谱他共有过五本。这开场白十分抓人。随后他写了四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时他二十多岁,原本是乐盲,忽然发现了西洋音乐的美好天地,又被古琴所吸引,他不信“古琴最难学”,也不信“梅庵”天书难解,就凭着王光祈一本《翻译琴谱之研究》,硬把书中一些小品翻译成五线谱,并借来一张“声如木石”的旧琴,开始自弹自赏。这以后没再接触古琴,主要兴趣也在西方古典乐,可每逢爱乐知已,总要怂恿人家听琴,因为他发现:不听古琴,就不会相信世上还有西方管弦乐所不可取代的奇妙乐器。接着写了他听《平沙落雁》和《潇湘水云》的亲身感受,尤其是后者,写得惊心动魄,结合了他在上海“孤岛”时期观史剧《正气歌》的体验,点出了音乐中的巨大内涵。他的文章是真正的美文,通篇是有情的叙述,几乎找不到抽象的概念,但其实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只不过如盐之在水,自然消融于骨子里了。他说,听乐而能引起“共振”,正如读画能感受到“湿闷空气”或“觉有暗香袭来”,这心理效应可以得到解释,并不玄虚。古乐产生于历史,“历史感犹如电击”,这是“乐中之史”,是它能打动人的深层原因。作者在这第一篇专栏文中写下的话,透露了他一生思考的大问题,这在他晚年又有重要发挥,可惜未能做成更大的文章。后文对古琴曲的逸佚与琴师的“手传心授”,以及古琴的生产制造以至“壮胆革新”,也谈了很内行的意见(他认为古琴上弦是麻烦事,似可改弦更法),这些意见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下面这段文字,在他笔下是颇具代表性的:
我之所以说琴有特殊功能,别的乐器不能及,根据在于:它虽然靠弹拨来发音,却能在不设品、柱的指板上通过移指、滑指的办法来变动其音高,从而取得完美的“圆滑奏”(legato)效果(但又不像“单弦拉戏”之类的单纯模拟唱腔与语调),向歌吟之声靠拢,有利于发挥歌唱性。再加上它能运用“散、实、泛”音不乏音响的对比与衔接,变幻其音色与浓淡。而“吟、猱、绰、注”等多种指法的应用,既强化了歌唱性,又形成了特殊韵味。初听古琴,会觉得它的音响并无耀眼的光彩(竖琴则相反);熟听,便像水墨画的“墨分五彩”,色调复杂微妙。种种特色,综合成了古琴的语言……
这种文字,没有大量听乐感受不行,没有对琴的亲手操作,没有对音乐原理的深入了解,也不可能写出。
第二篇专栏文是两个月以后,发在1989年第9期《读书》上的《如是我闻贝多芬》,从四十多年前自己初听《月光曲》展开全文。他在“文革”中被发配充军时,还斗胆夹带了两本九首交响乐的钢琴谱,以及一部俄文版“贝传”。从这样的传奇经历写到长期“听贝”、“读贝”的感想和思考,此文同样引人入胜。第三篇《一花一世界》,发表于同年12月号,写一组迷人的音乐小品,其中有《回想》,有《少女的祈祷》,有舒伯特《音乐的瞬间》、贝多芬《致爱丽丝》、门德尔松《春之歌》、圣桑《天鹅》……文章和这些小品一样可爱。到这时,辛丰年当真抓住了大批有心的读者。
人们这才由这个陌生的名字,由这个神秘的作者,反观他前几年出版的那本《乐迷闲话》,也才发现了它和普通的音乐知识普及读物的不同。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人传统,进入现代社会后,专家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五四”后那些大知识分子,包括鲁迅、胡适、周作人、钱锺书等,既是专家又是大文化人,这是“专家之上的文人”,他们的存在,对保持一个时代的高尚的文化氛围,至关重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书》杂志周围那批优秀作者,如吕叔湘、费孝通、张中行、金克木、舒芜、黄裳等,无一不是专家之上的文人——辛丰年也是其一。后来《读书》改弦更张,有一段时间努力突出“社会科学”,强调“专家化”,让年轻一代“专家”挤走“文人”,致使销路渐跌,刊物也没以前好看了,直到十年后才发现缺失并再作变更。其中如有失误,也就是看差了一点:专家之上的文人,事实上高于专家——那是须专家们修炼多年才可能(不是都能)达到的境界!
奇特经历,低调为人
在人们只知辛丰年之文而不知其人时,在复旦大学发生过一件趣事。中文系的吴中杰教授听说在读的博士生严锋的父亲从南通来,住在校内,这位老人很懂音乐。吴正愁找不到行家给自己的研究生谈谈音乐,就让严锋去请他父亲讲课。不料两天后严锋来报,其父不善交际,怕见生人,已逃回南通去了。到这时,吴教授才知这位老人就是辛丰年,他也因《读书》而迷上了辛丰年的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过辛丰年的书。不久后,吴教授由严锋陪同,专程到南通拜访了辛丰年,写出了《市嚣声中听雅乐》,发表在《文学报》。
辛丰年本名严格,他的笔名取自英语单词交响乐(symphony)的音译。1945年4月,他从上海乘小船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他先做文化教员,后又到文工团工作。他是个老而不大的干部,建国后实行行政级别制时,就一劳永逸地被定为十五级。几乎所有的老战友都说他对工作极为勤勉认真,对理想和事业也无限热忱。然而在“文革”中,因为说了几句关于林彪集团的话,便被打倒,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在砖瓦厂接受监督劳动。到了晚上,他就读鲁迅和《英语学习》等书。看书累了,就拿出小提琴拉几段,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林彪倒台后,得以平反,复员改转业。本可官复原职,但53岁的他提出提前退休,他要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这损失就是时间,自己的时间!退休手续办完,他拿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全买回来。要看的书实在太多,连吃饭时间他都在看书。还有就是听音乐。先是听韩国短波台的古典音乐,以后买了盘式录音机,又买了夏普四喇叭“立体声”,接着每天大录特录上海调频广播台的古典音乐。到1994年,有了CD唱机。因许多唱片买不起,他买了大量乐谱。读乐谱,可以演绎最新最美的演奏——那是在自己头脑中;当然最好能用乐器摆弄一番,1986年他买来一台钢琴,63岁的他开始学琴,一上来就弹舒伯特,弹肖邦。他学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增进对音乐的理解和体验。也就是在读书、听乐和练琴时,他开始酝酿一篇篇“门外读乐”的美文。
关于他的读书,有一点不得不说。他学历只有初中二年级,一切靠自学。他能通读俄文,精于英文。就在办好退休后,有朋友从远方寄来一部厚达1187页的原版《牛津乐友》,书是从图书馆借的,限期归还。他一看真是好书,便如饥似渴边读边抄(那时还没条件复印),因写中文比写英文快,他就读英文,写中文,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部厚书完整摘译了一遍,从而大大提高了阅读和翻译的水平。据杨燕迪说,辛丰年还曾借了保罗·亨利·朗的英文原版《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全本复印(复印件重达十几公斤),细细研读。此书后由杨燕迪等译成中文,有120万字。这位低调的老人,在南通尽其可能寻找全世界最好的音乐和书,用自学的英语读、抄、译……并将其中最好的内容,拌和着自己的艺术体验与生命体验,精心结构,反复推敲,奉献给天南海北从未谋面的同好。所以,他的文章,虽不离乐,却都是广义的“书话”。
“历史中的声音”
自2006年起,我有幸成为对晚年辛丰年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位编辑。他作文之认真、艰苦,到这时我才有真切体会。
其实这时,他已经不再听乐,对自己一生中花那么多时间听音乐,他有点后悔。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听音乐把读历史的时间占掉了,我有那么多书来不及读!盛世听乐,乱世读史,我应该读史。”他晚年的文章,集中于一个题目:历史中的声音。他写梁启超,写李叔同,写丘吉尔,写梁武帝,写夏丏尊,写陈歌辛,写苏东坡和张岱,看起来题材分散,其实都是写历史的关键时刻,所留下的让人难以忘怀的几句话,那是人的心声,也是历史的刻痕。他以自己听音乐的敏锐耳朵,在史书中寻觅这心声和刻痕。
辛丰年下笔极慢,文章不到最好,决不拿出来。看他发表的文字绚烂流畅,其实是一字字抠出来的,只是不留痕迹罢了。他每一文至少改三遍,每一遍都要一笔一画恭正抄齐,这是他的写作习惯,他就在这样的抄写中推敲文意,抹去生硬痕迹。晚年手抖,抄写更难,但仍坚持这么写。唐代苦吟诗人有“郊寒岛瘦”之说,《读书》的作者群中则惟有他和谷林先生有此“苦吟”之风。但谷林为文所取题目较小,读书极细却以趣味为主,不似辛丰年心怀“大志”而又逐字苦吟。如此看来,辛丰年是最“苦”的一位。但他苦而充实,毕生有追求,眼光一直看着远处。正如严锋所言:“他这一生过得很苦,也过得很好。”
因为他的情感、思想和他的“苦吟”,他留下的文章有独一无二之美,这是无可取代的。
(摘自《前辈们的秘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版,定价:1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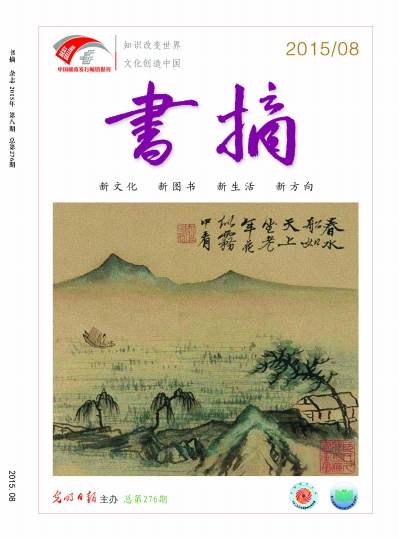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