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过去了。
我流浪在福建德化山区里,在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我还不明白世界上有一种叫做工资的东西,所以老板给我水平极差的三顿伙食已经十分满足。有一天,老板说我的头发长得已经很不像话,简直像个犯人的时候,居然给了我一块钱。我高高兴兴地去理了一个“分头”,剩下的七角钱在书店买了一本《昆明冬景》。
我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点意思也不懂。这我可真火了。我怎么可以一点也不懂呢?就这么七角钱?你还是我表叔,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呢?七角钱,你知不知道我这七角钱要派多少用场?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过?我可怜的七角钱……
德化出竹笋,柱子般粗一根,山民一人抬一根进城卖掉买盐回家。我们买来剁成丁子,抓两把米煮成一锅清粥,几个小孩一口气喝得精光,既不饱,也不补人,肚子胀了半天,胀完了,和没有吃过一样。半年多,我大腿跟小腿都肿了起来,脸也肿了;但人也长大了……
我是在学校跟一位姓吴的老师学的木刻,我那时是很自命不凡的,认为既然刻了木刻,就算是有了一个很好的倾向了。听说金华和丽水的一个木刻组织出现,就连忙把自己攒下来的一点钱寄去,算是入了正道,就更是自命不凡起来,而且还就地收了两个门徒。
堪惋惜的是,那两位好友其中之一给拉了壮丁,一个的媳妇给保长奸污受屈,我给他俩报了仇,就悄悄地离开了那个值得回忆的地方,不能再回去了。
※
在另一个地方遇见了一对夫妇,他们善心地收留我,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这个家真是田园诗一样善良和优美。我就住在他们收藏极丰富的书房里,那些书为我所有,我贪婪地吞嚼那些广阔的知识。夫妇俩给我文化上的指引,照顾我受过伤的心灵,生怕伤害了我极敏感的自尊心,总是小心地用商量的口气推荐给我系统性的书本。
“你可不可以看一下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你掌握了这一类型的各种知识,就会有一个全局的头脑。你还可以看看他写书的方法……”
“我觉得你读一点中外的历史、文化史,你就会觉得读起别的书来更有本领,更会吸收……”
在两位好人家里的两年,我过去短短的少年时光所读的书本一下子都觉醒了,都活跃起来。生活变得那么有意思,几乎是,生活里每一样事物,书本里都写过,都歌颂或诅咒过。每一本书都有另一本书做它的基础,那么一本一本串联起来,自古到今,成为庞大的有系统的宝藏。
※
以后,我拥有一个小小的书库,其中收集了从文表叔的几乎全部的著作。我不仅明白了他书中说过的话,他是那么深刻地了解故乡土地和人民的感情,也反映出他青少年时代储存的细腻的观察力和丰富的语言的魅力,对以后创作起过了不起的作用。对一个小学未毕业的人来说,这几乎是奇迹;而且坚信,人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只身来到上海,生活困难得相当可以了,幸好有几位前辈和好友的帮助和鼓舞,正如伊壁鸠鲁说过的“欢乐的贫困是美事”,工作还干得颇为起劲。先是在一个出版社的宿舍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然后住到一座庙里,然后又在一家中学教音乐和美术课。那地方在上海的郊区,每到周末,我就带着一些划好的木刻和油画到上海去,给几位能容忍我当时年轻的狂放作风的老人和朋友们去欣赏。记得曾经有过一次要把油画给一位前辈看看的时候,才发现不小心早已把油画遗落在公共汽车上了。生活穷困,不少前辈总是一手接过我的木刻稿子一手就交出了私人垫的预支稿费。记得一位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大上海这么大,黄永玉这么小。”天晓得我那时才二十一岁。
我已经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他的毛笔蝇头行草是很著名的,我收藏了将近三十年的来信,好几大捆,可惜在令人心疼的前些日子,都散失了。有关传统艺术系统知识和欣赏知识,大部分是他给我的。那一段时间,他用了许多精力在研究传统艺术,因此我也沾了不少的光。他为我打开了历史的窗子,使我有机会沐浴着祖国伟大传统艺术的光耀。在一九四六年或是一九四七年,他有过一篇长文章谈我的父母和我的行状,与其说是我的有趣的家世,不如说是我们乡土知识分子在大的历史变革中的写照。表面上,这文章有如山峦上抑扬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应的小协奏,实质上,这文章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与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马路上买到了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热闹的街肆中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打扰我,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
※
解放后,表叔是第一个要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人。不久,我和爱人梅溪带着一架相机和满满一皮挎包的钞票上北京来探望从文表叔和婶婶以及两个小表弟了。
表叔的家在沙滩中老胡同宿舍。一位叫石妈妈的保姆料理家务。我们为北方每天三餐要吃这么多面食而惊奇不已。
我是一个从来不会深思的懒汉。因为“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周一上学,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好久我才听说,表叔在“革大”的学习,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日子。他被派定要扭秧歌,要过组织生活。有时凭自己的一时高兴,带了一套精致的小茶具去请人喝茶时,却受到一顿奚落。他一定有很多作为一个老作家面对新事物有所不知、有所彷徨困惑的东西,为将要舍弃几十年所熟悉用惯的东西而深感惋惜痛苦。他热爱这个崭新的世界,从工作中他正确地估计到将有一番开拓式的轰轰烈烈、旷古未有的文化大发展,这与他素来的工作方式很对胃口。他热爱祖国的土地和人民,但新的社会新的观念对于他这个人能有多少了解?这需要多么细致地分析研究而谁又能把精力花在这么微小的个人哀乐上呢?在这个大时代里多少重要的工作正等着人做……在那一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婶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的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光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
我们在北京住了两个月不到就返回香港,通信中知道表叔已在“革大”毕业,并在历史博物馆开始新的工作。
两年后,我和梅溪就带着七个月大的孩子坐火车回到北京。
那是北方的二月天气。火车站还在大前门东边,车停下来,一个孤独的老人站在月台上迎接我们。
从文表叔十八岁的时候也是从前门车站下的车,他说他走出车站看见高耸的大前门时几乎吓坏了!
“啊!北京,我要来征服你了……”
时间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
比他晚了十年,我已经二十八岁才来到北京。
我们坐着古老的马车回到另一个新家,北新桥大头条十一号,他们已离开沙滩中老胡同两年多了。在那里,我们寄居下来。
※
从文表叔一家老是游徙不定。在旧社会他写过许多小说,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齐”。那么,他该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四合院的住屋了,没有;他只是把一些钱买古董文物,一下子玉器,一下子宋元旧锦、明式家具……精精光。买成习惯,送也成习惯,全搬到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去。有时连收条也没打一个。人知道他无所谓,索性捐赠者的姓名也省却了。
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的。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长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叨一些鼓励的话……他的工作是为展品写标签,无须用太多的脑子。但我为他那精密之极的脑子搁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我多么地不了解他,问他为什么不写小说;粗鲁的逼迫有时使他生气。
一位我们多年尊敬的、住在中南海的同志写了一封信给他,愿意为他的工作顺利出一点力气。我从旁观察,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凡事他总是想得太过朴素,以至许多年的话不知从何谈起。
保姆石妈妈的心灵的确像块石头。她老是强调从文表叔爱吃熟猪头肉夹冷馒头。实际上这是一种利用老人某种虚荣心的鼓励,而省了她自己做饭做菜的麻烦。从文表叔从来是一位精通可口饭菜的行家,但他总是以省事为宜,认为过分的吃食是浪费时间。每次回家小手绢里的确经常胀鼓鼓地包着不少猪头肉。
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学的工作定下来后,很快找到了住处,是在北京东城靠城边的一个名叫大雅宝的胡同,宿舍很大,一共三进院子。头一间房子是李苦禅夫妇和他的岳母,第二间是董希文一家,第三间是张仃夫妇。然后是第二个院子,第一家是我们,第二家是柳维和,第三家是程尚仁。再是第三个院子,第一家是李可染,第二家是范志超,第三家是袁迈,第四家是彦涵,接着就是后门了。院子大约有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孩子,我每天要有一部分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带他们一道玩,排着队,打着扎上一条小花手绢的旗帜上公园去。现在,这些孩子都长大了,经历过不少美丽和忧伤的日子。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了很亲密的关系。
※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刻一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不好看。为这幅插图,表叔特地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了我一顿:
“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三十岁了。没有想象,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
这给我的打击是很大的。我真感觉羞耻。将近三十年,好像昨天说的一样,我总是提心吊胆想到这些话,虽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
在从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岳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光潜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温存得很,亲切地谈着话,吃着客人带来的糖食。印象较深的是巴老伯(家里总那么称呼巴金先生),他带了一包鸡蛋糕来,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吃这些东西,缺了牙的腮帮动得很滑稽,一面低声地品评这东西不如另一家的好。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时候才能来北京一次,看这位在文学上早已敛羽的老朋友。
金岳霖先生的到来往往会使全家沸腾的。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裤,尤其怪异的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脑后捆起来。金先生是从文表叔的前辈,表弟们都叫他“金爷爷”。这位哲学家来家时不谈哲学,却从怀里掏出几个其大无匹的苹果来和表弟家里的苹果比赛,看谁的大(当然就留下来了)。或者和表弟妹们大讲福尔摩斯。老人们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信口说出的典故和数字,外行几乎不大相信其中的准确性。
表叔自己记性也非常好,但谈论现代科学所引用的数字明显地不准确,虽然是聊天,孩子们却很认真,抓着辫子就不放手,说爷爷今天讲的数字很多相似。表叔自己有时发觉了也会笑起来说:“怎么我今天讲的全是‘七’字?”(七十辆车皮,七万件文物,七百名干部调来搞文物,七个省市……)“文化大革命”时,那些“管”他的人员要他背毛主席语录,他也是一筹莫展。
我说他有非凡的记忆力,所有和他接触过的年轻朋友是无有不佩服的。他曾为我开过一项学术研究的一百多个书目,注明了出处和卷数以及大约页数。
他给中央美院讲过古代丝绸锦缎课,除了随带的珍贵古丝绸锦缎原件之外,几乎是空手而至,站在讲台上把近百的分期的断代信口讲出来。
※
他那么热衷于文物,我知道,那就离开他曾经朝夕相处近四十年的小说生涯越来越远了。解放后出版的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序言中有一句话:
“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
听起来真令人伤感……
有一年我在森林,我把森林的生活告诉他,不久就收到他一封毛笔蝇头行草的长信,他给我三点自己的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这几十年来,我都尝试着这么做。
(摘自《沈从文与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4月版,定价:3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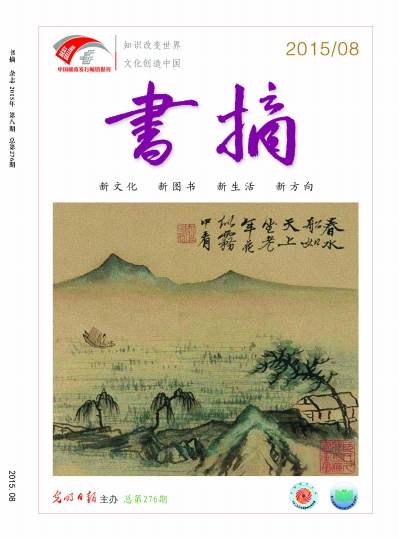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