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办事的知识分子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里的一位青年同事汝信说:“知识分子是不能办事的。”金岳霖深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自己就不能办事。“到清华,我比冯友兰先生早,可是,管行政事情的是冯先生,我办不了事。解放以前,学校的官我没有做过。”到了哲学所不久,金副所长就被准许在家待着,不必问政了。“显然,他们也发现我不能办事。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在这一点上,他甚是佩服清华同事陈岱孙,认为“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梅贻琦校长离校时,经常由陈代理校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校,但清华园已被日本军队破坏得不成样子,教员宿舍也成了养马的房子。梅贻琦知道陈岱孙的办事能力,于是派他先回京做恢复清华园的工作。陈先生当然不负众望,很快恢复原来秩序。“这就说明,真的知识分子是可以做工作的,可以办事的。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金先生话语间不无赞许。
那时的知识分子,确实有很多“能办事”的人才。不仅仅陈岱孙,梅贻琦本人也是一员干将。1942年,梅贻琦53岁,以清华校长的资格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南开校长是张伯苓,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但张伯苓在重庆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梦麟,蒋梦麟又将担子压给了梅贻琦。于是,整个联大校务就落到了三人中最年轻的梅贻琦身上。而梅贻琦干得也的确出色,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弦歌不辍,培养出一批人才。
1930年至1945年,蒋梦麟执掌北大。甫一上任,蒋梦麟便将刚刚北上的胡适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并制定出“校长治校,教授教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方针,大力延聘名教授,重振北大。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言此便“潸然涕下”,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何兆武回忆说,他的姐姐在北大化学系读书时,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被抓捕。过了两天,他父亲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写来的,大意是: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何先生说:“解放前,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出来保。”
傅斯年也是一位能办事的知识分子。抗战前,学术界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教授称为“老板”,当时北平学术圈内有三个老板: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从1928年起,傅斯年就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7年春,又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大校长。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傅斯年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此语绝非自夸。事实上傅斯年很清楚自己的底线。1946年,蒋介石欲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回信婉拒,并说自己只是一愚戆书生,“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并表示“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蒋梦麟曾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与当下的“仕而忧则学”完全两码事),查看一下当年国民政府高官的学历,可见一斑,如:行政院长翁文灏是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是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驻美大使胡适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柏林大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博士;司法部长王宠惠是耶鲁大学博士……当年知识分子从政,有其时代特征。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一帮知识分子就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于是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这种“好政府主义”初步显示出独立的自由精神,体现了现代中国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干涉政治的模式。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就曾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
但这只是一帮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事实上“好人政府”仅存在三个多月就垮台了。胡适深受打击,遂下决心“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好友丁文江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丁还说,如今“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丁文江本人正是一位“起而行”的人物,罗素曾评价他说:丁文江是我见过的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最是旧文人不自由
中国社会是个以家族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模式,也正因此,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家族制度成为罪魁祸首,受到诸如打倒孔家店、反封建、土改、四清、斗私批修、破四旧等一系列“革命话语”的冲击。曾有“五四”亲历者回忆说:“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作‘他你我’。后来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儿,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大家是平等的”,这生而为人的一句话,启蒙与觉醒的第一步,同时却也是宗法氏族的衰败之始,“旧时王谢”之家从此绝矣。随着世家大族在革命话语面前的日渐衰微,一种贵族精神也逐渐终结。
1949年后,经过有系统的教育、改造,一大批与“旧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旧知识分子”、“遗老遗少”们,纷纷与过去的家庭背景和知识体系决裂。费孝通说:知识分子接受了,认为过去的一套完全无用了,都不行了。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也都这样,觉得思想非变不可了。而且认为是原罪,“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
桐乡文人丰子恺,风神潇洒,淡泊名利,倾心于艺术,皈依于佛教,一直在他自己营造的宁静祥和的世界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被世人称为“21世纪的陶渊明”,“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然而,激变后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了陶渊明的生存环境,1952年7月,丰子恺写了一份《检查我的思想》说:“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北大老教授汤用彤自信得近于傲慢,解放前,得知其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奖时,满脸不高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钱穆谈起汤用彤来,也是感叹不已,赞其为“纯儒之典型”。解放后,《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时,汤写了个后记,里面说到自己“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看后说:“这是降低身份。”
在时代的高压之下,也有一些出身旧世大族的文人们,没有使自己的个性自觉地消失,“旧”的根基,家族的生活传承,使他们本能地坚守住了一个文人的底线,自我的异质性没有被那个庞大的同质性的洪流所吞没。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复信中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在“唯马首是瞻”的高度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之下,像陈寅恪那样出身书香门第的世家学者,不是戴帽子,就是靠边站,能够“默默者存”已属不易,想要“继承家学”,再作研究,就难免会挨批。旧式才子俞平伯,幼承庭训,13岁读《红楼》,15岁便考入北大,师从黄侃。俞一生成也红楼败也红楼,经毛泽东一批,马上名气远播,妇孺皆知。“文革”期间,他被下放河南明岗干校,远近几十里的村民像赶集一般纷纷赶来观赏他的尊容,如赏猴戏。圆圆脸的俞先生涵养极好,只是袖手端坐,任凭老乡们挤着观看,品头论足。
今天,在这个大众文化喧嚣沸腾的时代,原子式的个人面临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和人伦归宿的虚无感,对传统伦理价值的追寻与认同日益强烈。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做三辈子学吃,五辈子学穿,贵族不是一天所能养成的。如今,怎样重新做一个贵族,怎样传承那种维护尊严、爱人爱己的贵族精神,并以此精神来对抗群氓、对抗粗鄙,是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仁不让
《论语·卫灵公》语“当仁,不让于师”与西哲“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义理相通, “当仁不让,吾何辞哉”,敢承担,不推辞。这道理讲起来好听,但做起来往往荒腔走板,变作了文人空自许。
民国学者黄侃一生颇多自许,好臧否人物而少许可者。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期间,学校规定师生均须佩戴识别证,否则不得入校。某日,他到校上课,新来的校警不认识他,拒绝他入校。黄说:“我是黄季刚教授,到学校上课的。”校警指着自己的识别证说:“你又不戴识别证,我怎么知道你是教授呢?”黄大怒,把皮包和讲义塞给校警,说道:“你有识别证,那你去上课吧!”校警当然不敢在黄侃面前“当仁不让”,但有敢的。中央大学校长为款待黄侃,特置一小沙发在教授休息室。其他教授多有耳闻,皆视而不见。某日,词曲家吴梅课毕来休息室,见此沙发空着,便坐下。黄侃也刚好课毕走进来,一见吴梅坐上了小沙发,大怒:“你凭什么坐在这里?”吴款款答曰:“我凭词曲坐在这里。”
诗人孙大雨曾以韵文翻译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颇瞧不起其他新诗人。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任教时,兴之所至,先在黑板上抄一段闻一多的诗,连呼“狗屁”;再抄一段徐志摩的诗,连呼“狗屁”;最后再抄一段自己的诗,击节称赞良久,开始心满意足地讲课。而闻一多又何尝不是一位狂士。据说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讲唐诗,进教室先不讲课,而是掏出烟斗来问学生:“哪位吸?”学生们自然不敢受用。于是,闻自己点上一支,长长舒出一口烟雾后,朗声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孔子曾跟他的学生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就是说,你要努力提高修养,立志学大道办大事,不要在一粥一饭之间谋生活。后世儒者,也都以君子儒自勉。当代大儒熊十力一生践行“君子儒”,但熊氏也深知自己性情峻切,口无遮拦,缺少一份儒者的典雅。但他决计不去改正,任谁劝告也是“不欲改”。牟宗三回忆初见其师熊十力时情形:“……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气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忽然听见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林宰平时与熊十力过从甚密,他曾批评熊氏老爱以师道自居。熊说:“我有所得嘛,为什么不居?”熊十力爱吃肉。某次,熊十力在一位朋友家吃饭,一个小孩子要吃桌上的一块肉,被熊十力抢了过来,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说完坦然吃下。
熊十力和陈铭枢是在南京学佛时结识的好友。熊在大学时,陈一定要每月寄钱30元表示资助。有一次陈的会计忘了寄钱,熊十力立刻写了封信,上面写了一百来个“王八蛋”。陈看信后,马上补寄钱过去。熊十力通脱旷达,不事雕饰,但大事不糊涂。某次,陈铭枢去杭州看望熊十力,当时正是“一·二八事变”前夕,风雨如晦。两人一见,熊劈面就打陈铭枢,骂陈不在上海准备抵抗,居然跑到杭州游山玩水来了。有一次,殷海光去北平拜访熊十力。殷问他:“您老人家喜不喜欢恭维?”“我吗,”熊打着湖北黄冈腔答道,“那要看恭维得是否恰合分际。要是恭维得恰合分际,我引为知己,当然高兴。要是不合分际,说些浮词泛语,我很厌烦。”他在说“恰合分际”四字时,大拇指和食指捏拢,做了一个很优美而准确的手势。
“恰合分际”的恭维确为难得,算是“知己之言”。恭维得当,往往使自许者也不得不谦虚起来。20世纪80年代初,李慎之读完四卷钱著《管锥编》后,敬佩之余,登门道贺,说自己特别佩服钱锺书的“自说自话”,文中无一趋时语。钱听后颇为受用,淡淡一笑,答曰:“天机不可泄漏。”
(摘自《说多了就是传奇》,新星出版社2014年9月版,定价: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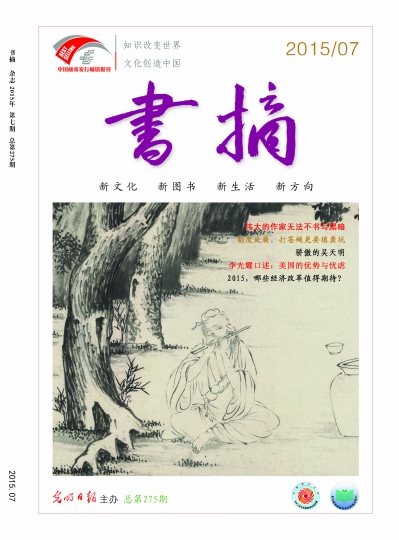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