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起是哪一年初识龚明德了。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在不认识他之前,已经知道了他的大名,仿佛是因为《〈围城〉汇校本》的事,在报上折腾得沸沸扬扬的。我有一本红色封皮的《〈围城〉汇校本》,翻了翻,当时觉得龚明德是一个傻蛋,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费了这么大的劲,搞了这样一本书,人家记得的还是钱锺书。可是呢,钱锺书也不买账,还与龚明德与四川文艺出版社打官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龚明德和他所在的出版社输了,大约赔了七万元钱。我想,有的人是愿意看看自己以前的文字的,有的人则不愿意,钱锺书可能就属于不愿意这一类。我不愿意看,你却把我抖出来,我不开心了,就和你打官司,就叫你赔款,如此而已。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龚明德寄来的一本《新文学散札》,内附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六场绝缘斋 龚明德”,下面是他的家庭地址和邮编,但是没有单位地址,也没有电话。“六场绝缘斋”是龚明德的书斋名。“六场”者何,有多种释说。据龚明德散文《寂寞书斋》以及他的老朋友、老同学毛翰的文章,“六场”是官场、商场、情场、赛场、赌场、舞场。六场绝缘,当然是不当官不与当官的人勾搭、不做生意不与生意人来往、不搞婚外恋、不与人斗智较力等等,是一个近乎愚直的文人的宣言。但北京的谷林,最近有一文论及“六场绝缘斋”,说是与一切干扰文化建设的言行绝缘之意,当更准确,正如龚明德《我的书房》一文所讲,“六场的‘六’,与六亲不认的‘六’是一个含义。”龚明德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出版社工作,但用的信纸和信封却都是自制的,这一点,符合冰心的要求。有孩子用父母单位的信纸给冰心写信,冰心还专门去信说这样不妥。龚明德是因为我写有《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一书,觉得我们都喜欢“新文学”,所以给我寄他的书的。我很快回赠了他《鲁迅:最受诬蔑的人》。我们就这样相识了。
这期间,我们偶有书信往来。我们往来书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多是这样的,比如,他责编了《董桥文录》,寄一本给我,附几句话,就是这样。
1999年,我到成都出差,自然要去拜会龚明德。那天大约是周末吧,我向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晏开祥先生打听龚明德家的电话,晏开祥说,龚明德的电话是不公开的,虽然他们是同事,也不知道他家的号码。我又问了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颜小鹂小姐,她说,她也不知道。先前,她通过龚明德的家人曾搞到他的旧号码,打了一个电话给龚明德,龚明德很吃惊地问她,你是怎么搞到电话的?龚明德有点像在搞地下工作,不久,他就把电话改了。这种说法有点夸张,龚明德是不是真有这样的“逸闻趣事”,我也没有向他证实过。那次,我本来想用周末时间见见他的,终于没有见成。
周一,我上了他办公室。我说了电话的事,他说是的,他不随便给别人电话,只给该给的人。边说,他边为我写他家的电话号码。哦,我是他该给的人之一。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很多。在他办公室,我们小聊了一会儿,他忙着找书送我。他送了三本他责编的书,都是他特意做的毛边本,其中还有一本百岁老人章克标题签的《文坛登龙术》。我非常感谢他的盛意,这几本书我都好好收藏着。
晚上他请我吃饭。他也会请客吃饭?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自然说了几句客气话,他不容我多言,拖着我就走。我们在一家电影院旁边的小饭馆落座。他说,他去打一个电话。我问怎么了?他说他不会点菜,要叫他爱人来点菜。我说我们随便吃一点吧。他带着隆重的神情,摆摆手。说是不行,要他爱人来点。
接着我们就聊起了闲天。他说话时,我认真地观察他。他理着平头,头上花花白白,有了勤于学问的辛酸。他把皱巴巴的黑外套脱下,现出了里面草绿色的毛衣,我发现,他的似乎不是全毛的毛衣已经破损,弯起手时,肘处裸露了一大块。我的感觉是,他从神情到外貌都有点像陈景润,是一个不懂生活的人。
他的妻子来了,很快为我们点了菜。她也坐着吃了一会儿。龚明德傻笑着对她说:“你先走吧。我们要说话哩。”我连忙说,一起吃饭,别急着走呀。她不说什么,很善解人意地笑着。又过了一会儿,她说她有事,先走了。事是肯定没事的,她是被龚明德“赶走”的。不过也好。她陪着我们吃饭,也累。龚明德的太太在省直机关工作,望着她远去,我想,她能容忍龚明德的非世俗化生活,应是不平凡的女性。
龚明德的笑,是标准的憨笑,憨笑之外,仿佛还有点在聪明人眼里的那种傻笑,从根本上说,他的笑极像孩子的笑。那时,成都正冷,他率真地对我笑着,我感觉从心底升起一股暖意。
走出饭馆,边上正是电影院,他提议说:“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客随主便,我们就去看电影了。电影开场前他说:“我有十几年没有看电影了。”我说,我也很久没有看电影了。电影院里男男女女,相依相偎,前面后面,还升腾起香水味。我们两个大男人也在小影院里看电影,我感觉有点滑稽。我们也没问是什么电影,什么电影都无所谓的,买了票就开看了。说来好玩,那天上演的是动画片《人猿泰山》。电影开始时,我们先是相视一笑,那意思彼此都很明白,就是说,我们怎么会来看动画片?就这样,我们进入了久违的动画世界。
哇噻,这是一部不得了的进口动画片,把我们的魂都给勾去了,世界上还真有这么好的电影啊!看罢电影,走出影院,我们像两个傻孩子,都不说话。走出十几米了,龚明德突然说:“我们再看一遍!”那不是商量的口气,充满了肯定意味。我当然乐意。于是,两个很不时髦的人物再一次进了小影院,再看了一遍《人猿泰山》。
电影看完,夜和龚明德的学问一样深沉。我们握握手,也没有多余的话要说,各自东西。他真是一个深沉的人,我却是一个假装深沉的人。太深沉了,太累了,我们都被童话般的《人猿泰山》唤起了深藏在灵魂某处的单纯,唤起了童年的梦和梦一般的记忆。
此后,我们在福州见过一次面,他来参加巴金研讨会,那天晚上在场的还有他的女社长罗韵希,我们谈的多是出版问题。
这段时间,我有着强烈的冲动,想写一写龚明德。这原因有三,一是不久前他打电话,让我到福建教育出版社为他买《钱玄同日记》和《鲁迅纪念馆馆藏现代名家手札》线装本,两套书要四五千元,这让我想起了他那破破烂烂的毛衣;二是我到上海出差时,在上海社科院潘颂德先生那里得知,龚明德简直生活在书的海洋中,他家里容不下一切现代的物质文明,却挤满了无以计数的书;三是我最近要筹备创办一本新刊,向一些朋友征集刊名,自然也向龚明德征集,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出版广场》如交你抓,依我看,还是要往‘雅’的方面靠。‘俗’的刊物太多了,但真的‘俗’人是不自己订阅刊物的。只要一‘雅’,你的杂志就会很快引来一群优质作文的人。……我一直不开窍,在出版社二十多年,坚持印高品位书,宁可无奖金。我每年比别人要少拿六七万元,也就是说,不拿奖金。”龚明德不是人,他是个“书人”,做书的人、写书的人、读书的人。
我取“守望者”为篇名,也许与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有不近相同的地方。我要表达的意思是,龚明德是一个极有孩子气的人,他兀兀穷年,守着他的田地,他的精神家园。他埋头编书,写书,读书,他笑傲花天酒地,冷眼白领时尚。他瞅着他的自留地边上的山坡,坡上开满了桃花、茶花和不知名的花,万花丛中,鸟儿问答,在探讨着地球何以成为一个村庄;山坡下,水在流着,还有鱼儿在水中漫步,龚明德灿烂地淘气地笑着,满心满目全是他的“昨日书香”。
(摘自《醉眼看人》,青岛出版社2014年9月,定价:4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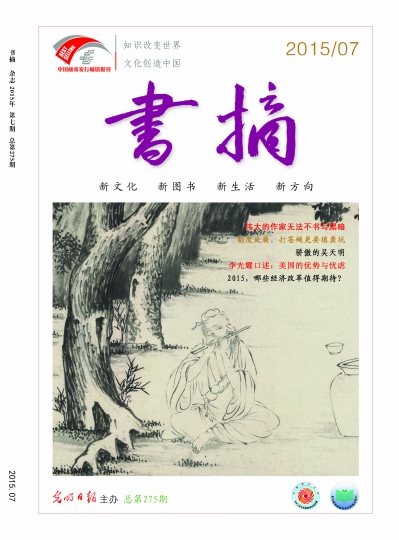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