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节过后,湘中山川草木刚从冰雪灾害中渐渐复苏。我回到了别了数年的家乡——湖南省新邵县言栗乡了田村。水泥马路已经铺设到家门口,“村村通”看来有些成效。山沟里多了好些新房,外面贴着俗气的瓷砖,这些多是主人南下打工攒下的辛苦钱盖下的,偶尔能在新屋前看到挂有广东牌照的汽车。回想起十九年前自己去上大学,背着行李走了好几里山路才在公路边挡了一辆农用车,辗转进城,坐上北上的火车。
到家后第一天晚上,族上三位爷爷辈的老人相约前来,他们中间最老的已过八十,最年轻的和我父亲同岁,也到了古稀之年。这几位老人的儿孙也多在广东打工,因为这年开春的大雪,多半滞留在广东过年。平常他们总和家父一起闲聊,父亲在他们这些人中间算是个文化人——读了三年私塾,新政建立后又读完高小,后出去学医,培养的儿女也算成器,待人接物称得上平和公道,因此在全族中威望较高,本房共有的一份族谱归家父保管。这份家谱是1986年重修的,用的是黄纸、竖排、锡印的传统工艺,封面上印着“李氏四修族谱”的隶字,扉页上盖着“陇西堂”的篆文印章。
我还记得族谱修好当时,舞着龙灯往各房护送,各房摆酒庆贺的情形。那时我念高一,一心只想着考上大学,离开这个闭塞贫穷的山村,对那几十本存放在樟木箱里的族谱不当回事,连翻阅的兴趣也没有。
几位爷爷前来,是知道我从北京回家了,承蒙他们一向谬奖,认为我是本族书读得好的后辈,想让我看一份族谱的补充材料,同时询问一下,按族谱三十年一修的惯例,有没有五修族谱的可能。
四修族谱,总其事者是另一房的席珪先生,他和我高祖父一辈。他的老书读得好,也读过新式中学。抗战爆发后,响应民国政府“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投奔同县老乡廖耀湘将军的麾下,远赴滇缅边境地区参加抗战。经历九死一生,侥幸回到故土,就赶上了政权鼎革后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被管制数年。我幼时放牛时,见过他几面。此番回家,听父亲说他已于一年前故去。1986年四修族谱时,距离1946年三修族谱已四十年,其间发生沧桑巨变,各房族谱在“破旧”的洪流中多被烧毁,好不容易找到一部残本将族谱续上,然而本族200年以前的脉络中断了。在遗憾之余,席珪先生辞世前二十年内一直在寻找本族的来源,几年前找到了一份文本,通过参校甄别终于弄清了本族的脉络,印了一份族谱补充资料送到各房。不久后,便遽归道山。
这份补充史料,不过是用繁体字和半文半白写就,本房在乡老人包括家父也不能完全看明白,只是说族谱的源头找到了。
拿着这份三页纸的材料,我一句一句翻译给几位长辈听。告诉他们,本族发源于唐代忠武王李晟,宋代熙宁间由吉安来邵阳高坪,和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李文是同族,在清末和李文所在的龙溪铺李氏花开两枝,各修族谱。
席珪公在篇末写道:“生齿日繁,若不汇而纪之,难免有苏子途人之忧。缘联遐迩宗系,志诸谱端,俾来裔披览,虽异地犹同一室。吁登堂念祖,修谱溯源,千秋不忘原首,是予之诚意也。”
对于几位爷爷五修族谱的提议,我不置可否。我深知近一个甲子,尤其是这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宗族为重要组织的农村社会和清末甚至民国时期完全不一样了。不但年轻人多在外地求学、打工,即使回到故乡,对家族的认同感和六十年前的先辈不能同日而语。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到来的今天,延续谱牒文化,坚守宗族共同体理念,已变得十分艰难。但席珪公的这几句话让我很有感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一个耄耋老人去寻觅本族族谱的源头?
因为几位爷爷的来访,我第二天早晨起来便决定将那几十本族谱翻阅一遍。族谱的体例很有意思,大约参考了国史修撰。第一卷是“封诰旌表”,即本族历史上某人接到朝廷的诰封、某人受过的旌表,所有的公文全部照录,以此彰显政治正确,也是一种炫耀。后面的卷册除各房宗系、人名辑录外,还有《迁徙志》、《艺文志》、《灾异志》、《山水志》等。各个时代有功名的人,都有资格在族谱中附有一篇传记。
通过几天的阅读,我发现二修族谱的主事者维翰公和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大历史有着联系。维翰公那一房住在本县白水洞,白水洞是本邑一大胜景,其景若《桃花源》所载:两悬崖对峙中有一小道,入小道往前走,见一小盆地,四壁青翠环绕,有飞瀑溪流。族谱《山水志》卷中详细记载了不同时期文人对此地的称颂。山水之秀化作人杰,此地李氏在本族中为人文最为荟萃。维翰公字艺渊,举人功名,和樊锥等人一起在邵阳主持过维新事业,当过南昌知府,署理江淮道,主管过湘省的盐业。在南昌时他修缮过斑衣娱亲的老莱子遗址,自己的堂名之为“慕莱堂”。族谱中记录有他修白水洞义学,慕莱堂落成以及父母寿诞时,当时和他过从的名人的祝贺诗词,有刘坤一、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等的,乃当时湘省人物之翘楚。秋瑾的父亲秋寿南是他的下属。后来我上网查询,查到秋瑾还是个十八岁的女孩时,写过一首词《临江仙·题李艺垣(“垣”为“渊”之误)(慕莱堂集)》祝贺李艺渊的文集刊行,词曰:“忆昔椿萱同茂日,登堂喜舞莱衣。而今风木动哀思,音容悲已邈,犹记抱儿时。南望白云亲舍在,故乡回首凄凄。慕莱堂上征歌辞,弟昆分两地,愁读《蓼莪》诗。”
族谱中有一篇维翰公自叙主持二修族谱的艰难。这次修谱成功后已是1912年新春,维翰公在过去的辛亥年中目睹清室逊位、民国建立,他曾避祸于沪上。作为一位前清官员,字里行间流露出其内心的痛苦。他几年后辞世,没能目睹上世纪20年代湘中农村狂飙席卷的大变局。这或许是种幸运。
本族二修族谱成功是帝制刚刚覆亡的1912年,三修族谱是抗战胜利的1946年,四修族谱则是改革开放进行有年且湘中农村从人民公社那种僵化体制下慢慢恢复生气的1986年。这三个年份,可以看作中国近世百年的三个时间坐标,坐标之间的每个区段差不多是三四十年。考察这百年湘中农村的变化,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宗族共同体观念日益稀薄,农村各项资源被外部的权力操纵的强度加剧,农村精英日益凋零,农耕文明的自信心受到毁灭性摧残。
在这种百年巨变中,本族祖辈中那些有文化责任感的精英,尚能在社会动荡的空隙中修撰族谱。对这些先辈,我在心中暗表崇敬之情。
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土地承包给各家各户,那时候农村最流行的风潮是“复古”:集资修族谱。农村老人的丧礼采取传统的方式,请道士和尚作法,祭奠仪式按照古礼。年末各大姓舞龙灯,清明集体祭祖成风,不时引发宗族冲突。
现在想来,这是政治权力主导的农村秩序出现问题后,农村人自然地到传统中寻找修补的资源。人民公社体制是公权力强加给广大农民的,这种不基于真实意愿的集体组合注定没有生命力,更不会造福于人,只能是广大农民的桎梏。公社散了,地分了,重新找回宗族的传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几年,湘中农村一个突出问题:重续的传统秩序和权力安排的秩序之冲突,其最易见的是因坟山引发宗族冲突。1949年前,湘中农村各大家族基本上有自己的坟山,这是全族共有财产,阖族长幼会珍惜坟山的一草一木。到人民公社时期,田土、山林的划分是就近原则,方便生产。张家的坟山很可能划归以王姓为主体的生产队,甚至跨越了公社的界限。在人民公社统管农村社会一切的时代,在强大的政治权力下,各族不敢置喙。一旦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经济解散,土地由农户承包,那些承包了并非本族祖坟所在山地的农民没有善待外姓祖坟的自觉,于是在坟旁沤肥,种菜的事很多,而祖坟山原属的宗族当然不干了,认为这是破坏风水、藐视本族之举,会利用集体祭祖的机会踏平菜地,从而引发冲突。这种事不能简单视为“封建迷信”回潮,而是官方安排的秩序在新的历史时期遭到了传统的挑战。就承包坟山土地的农户来说,菜地现在是他家的,他的权益不能被侵犯;对于坟山所埋者的后裔来说,他们维护祖坟也无可厚非。在1949年前坟山产权所有者和所埋者后人的身份是统一的,当然没有矛盾。这种冲突最后还是靠农村人自己的智慧解决,有的是承包地置换,将坟山的田土置换为本族人手中;有的是双方宗族的长老出面,经过协商达成协议,确保尊重别族的祖坟——在这点上是可以沟通的,因为每一宗族都有祖坟,都需要得到尊重,人同此心。
重修族谱在这个时候的盛行,是重续宗族传统的标志性行为。族谱,实际上是一份家族共同体的章程或者契约性质的文本,宗族成员凭借族谱彼此获得身份认同。同时,宗族成员也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享受总宗族的庇护,并有保护宗族坟山、尊重族规,维护本族声誉的义务。
然而,这种赓续与重建只是三千多年农耕文明的回光返照。随着各宗族老人的一个个故去,年轻人则成群结队南下打工,农村已失去活力,严格地说,没有年轻人为主体的社会是畸形的。此时,宗族自我管理的模式不会再有生命力,而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由于制度安排的不恰当,以及农村社会结构的残缺,又没有发挥其该有的作用。以宗族管理为主的乡村秩序式微的今天,建立一种良性的农村自我管理的秩序还长路漫漫。
回京前,望着老家堂屋里装家谱的樟木箱子,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可能是本族最后一个版本的族谱,再次修族谱已经没有了适宜的土壤。(补注:我当时的判断过于悲观,在2012年夏天,吾族在一些热心的宗亲努力下五修族谱成功。)
2014年清明节,我又回到故乡为祖先扫墓挂青。期间去看熟识多年的一位朋友,开车来接我的是乡政府一位基层官员。在车上一聊,他和我同族,互报彼此的辈分,他是“基”字辈,和我祖父同辈份。我大呼“爷爷辈开车接我,不敢当”。于是他向我介绍了2013年竣工的本族五修族谱,而他是这项“工程”的重要义工。本次修谱的资金主要来源是本镇一位企业家族叔。族谱修成的典礼上,有四川、贵州、广西的宗亲前来接谱。一位祖上康熙年间从宝庆府迁往四川的宗亲,在典礼上深情地说:“今天,我们在四川的几万人总算找到了自己的根。”那一刻,令所有在场的人动容。
(摘自《找不回的故乡》,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版,定价:3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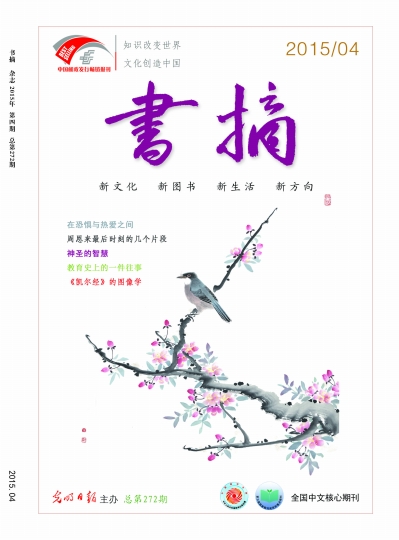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