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犬儒主义占据着不容忽视的支配地位。这种犬儒主义支配下的中国当代青春文化或低眉顺眼,或少年老成,或虚假励志,以一种自欺欺人、逆来顺受的姿态抚慰着青年的心,也麻醉着青年的心。
“小时代”的犬儒主义
2007年底,“青春教主”郭敬明推出了《小时代》。不久,《小时代》登上《人民文学》总600期“新锐专号”(2009年第8期)。2013年由郭敬明亲任编导的电影《小时代》(共三部)陆续推出,不但连续创造票房奇迹,更使其影响力跃出青春文化圈,席卷全社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郭敬明的作家资格,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小时代”三个字,一语道破了我们时代的某种精神状况,其精准的概括力,远远超过了众多著名作家的“时代大书”。
何谓“小时代”?恐怕难有准确的定义。个人的、细小的、物欲的、功利的……“小时代”对应的应该是宏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里,历史有宏大叙事,社会有整体价值,人类有共同愿景。“小时代”诞生的前提是“大时代”的崩溃解体,这一点,郭敬明们未必体会深刻——当他们尚在童年中时,历史已被宣布“终结”。将超越性的欲望和能量全部用于过个人的小日子,顺应消费主义的膨胀。于是,我们进入了“小时代”。
表面上看,“小时代人”很像福山所说的“最后之人”。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结”是福音,也是悲哀,因为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抗衡,在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全世界将日益成为一个同质化的社会。人们的“气魄”尽失,只剩下欲望和理性,成为“最后之人”,就像是尼采说的“末人”,“没有胸膛的人”,所有关乎勇气、理想、想象力的奋斗,都转化为餍足消费以及解决琐碎技术问题的努力。但事实上,“小时代人”与“最后之人”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区别在于是否还具有人之为人的尊严。
福山“最后之人”的说法来自黑格尔的自然状态下“第一人”的概念。在黑格尔看来,人和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是获得他人承认的需要,就是“自尊”。寻求承认的欲望驱使两个原始的战士决斗,最终,那个爱荣誉胜于爱生命的人成为了主人,成为了“第一人”,而那个屈服于死亡本能恐惧的人成为奴隶。在那些不是为了食物、住所、安全,而是为了纯粹名声的“承认斗争”中,黑格尔看到了人类自由的曙光,并认为这种感情推动着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在这种以“承认斗争”为基础的历史观里,“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所有人获得了所有人的承认。所谓“最后之人”,是指最后获得承认的人,也就是尼采所说的“赢得胜利的奴隶”。
如果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状态下的“最后之人”是最后摆脱了奴隶状态的人,在“历史板结”下的“小时代人”则是接受奴隶状态的人。历史没有终结,但我们已经放弃反抗。如此,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安抚自尊?尊严问题,如果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命题,那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于是,我们需要犬儒主义。
现代犬儒主义与古典犬儒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再是愤世嫉俗,而是玩世不恭。既然世界是不可改变的,那还有什么可说的?牢骚尽管牢骚,冷嘲尽管冷嘲,但一切最好以搞笑的方式进行。愤怒者最愚蠢,搞笑者最聪明。现代犬儒主义为中国当代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语)们开创的最大方便之门便是扫清了道德底线,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是要不得的。一切权力者的游戏都是应奋力加入的,为此屈膝是正常礼节。
在今日中国,犬儒主义不仅是一种流行性的文化,更是一种非官方的意识形态,是那种不是为了掩盖事实而是为了建构幻象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最为基本的定义出自《资本论》。书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但时过境迁之后,定义发生了变化:“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今日中国最走红的文艺作品,从“宫斗剧”到谍战片,从官场小说到各种攻略,往往是在悬置价值的前提下,教导人如何狡猾地生存,成功才是硬道理。
毕竟,郭敬明的成功之路是难以复制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屌丝”。成功不敢,舒服就好了。然而,青春的血总是热的,年轻人的腰杆总要挺得更直一些。于是,在他们自我创作的青春文化里,在表面张扬之下,有一种特别低回的自我抚慰,一种特别执著的自我麻醉。让热血温吞下来,让骨质松软下来,学习如何做一条舒服的狗。
“80后”的“精神奴役创伤”
戴锦华教授对“后冷战之后”的描述:“这是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作为唯一模式、唯一出路、唯一可能、唯一价值、唯一选择的时代。”
作为“小时代”的“原住民”,“80后”特殊的悲哀是,他们的时代感几乎是封闭的,从前的很多事,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大都是独生子女,是中国结束物质匮乏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从小吃得好,穿得好,没见过粮票布票,却也没怎么听说过“自由平等是天赋人权”——或许知道,但只在概念上,就如我一位“85后”学生所说的,“听说过,没见过,像鬼一样”。在一个“拼爹”的时代,他们从小必须接受没有理由的失败。当班主任把小红花颁给不该得到的同学时,他们被告知不要问为什么。但对于他们绝大多数人而言,其实无爹可拼。“80后”的父母大多是“50后”——青年下乡、中年下岗的一代。他们承担着社会主义最沉重的债务,子女又赶上了原始积累期。无怪乎在他们很多人的精神殿堂里,金钱是唯一的真神。其实,它是最大的怪兽,咬得每一个人无处藏身,但因为没有别的神可拜,只能匍匐在它的脚下,并且告诉自己“我相信”!
这就是我看《小时代》最难受的地方。我分明在美男俊女鲜衣美食的缤纷画面下,看到了赤裸裸的金钱奴隶制,感受到了被压迫者的压抑和屈服者的屈辱,但这份压抑屈辱完全不能指望在影片内得到抚慰。大家似乎都浑然不觉(或者觉得理所当然)——编导没有感觉,影片里的人物没有感觉,和我一起看电影的学生们也没有感觉。
影片以林萧为视角,这是一个出身弄堂的平民少女,她像是传统叙事中的灰姑娘,也应该是一个“成长人物”。她生活中有两个“大魔头”,一个是实习公司的老板宫洺,一个是闺蜜中的“老大”顾里,他们都是出身豪门的金钱信徒,不但有钱有势,而且信奉有钱就应该有势。影片用大量细节表现了他们的高傲、冷漠、刻薄以及怪癖,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平等的概念,下属就是奴隶,闺蜜就是跟班。在传统的叙事中,这样两座大山的出现就是用来被推翻的,人们期待着他们被成长中的主人公征服凌虐,或嘲弄戏谑,一抒不平之气。然而,什么都没有。从始至终,这两座大山巍然耸立,而且越来越高大,越来越完美。他们不但是最有钱的,而且是最精英的。他们傲慢的背后是责任担当,苛刻的背后是品质保证,刻薄的背后是刀子嘴豆腐心。在所有人都惊慌无措的时刻,他们是拯救者,是大靠山。于是,他们的羞辱变得可以忍受,怪癖甚至有点可爱。而林萧们不但是较贫穷的,而且是较低等的,她们永远以精神上的弱智和身体上的出丑而表现出某种“低贱的无辜”,陪衬着,搞笑着,以此完成对有钱有势者的顺服膜拜。
“爱上征服者”的心理模式,在“金钱奴隶制”统治的“小时代”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心理模式。“歌者当歌,不管好时代坏时代;有人瞩目就好,不管大时代小时代”(电影《小时代》片尾曲《小小时代》)。
2014年暑期档的精彩大戏是韩寒的《后会无期》PK郭敬明的《小时代•3》,一向被认为“文化层次较高”的韩寒粉丝期待着一次精神俯视。结果恐怕令不少人失望。在我看来,在这场PK中,韩寒彻底败给了郭敬明,不是输在票房,不是输在编导水准,而是输在了韩寒最看重的价值观上。韩寒拿什么和郭敬明的“金钱法则”对抗?离开了“公知”的话语体系,褪掉了“愤青”的反抗性,所谓的“另类”就只剩下港台腔包裹的“文青腔”,只是波西米亚式的肮脏邋遢和“二逼青年”的不靠谱。“亚文化”最核心的特征是抵抗性,从十九世纪中期的波斯米亚人,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文艺青年”的反抗一直是以资本主义主流价值为明确目标的,并且有乌托邦理想的支持。他们知道自己反抗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后会无期》里的“文艺青年”到底想要什么呢?恐怕他们连自己想反抗什么都不知道。所有“高富帅”拥有的,金钱、美女、出人头地,其实都是他们想要的,他们要“反抗”的其实只是“普通青年”生活的常规、烦闷、窘迫,但一切可以用来反抗常规的东西——浪漫的爱情、追星的梦想,都在影片内部受到嘲弄,不是骗局就是不靠谱。当那个蓬头垢面、眼光发直的乡村教师摇身一变为“文艺范儿”的畅销书作家时,让人感到又是一个郭敬明。
每一次“主流价值观”的大获全胜都由几个“回头浪子”收关,韩寒不过重复了当年诸多“嬉皮士”前辈“青年叛逆、中年主流”的老路,再一次告诉人们所谓“文青”的“后会无期”。
结语
如果说“小时代”是犬儒主义者的时代,那么这些胜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幸福吗?
小说《小时代》的结尾是个悲剧性的结局。当一切矛盾都化解了,一切故事都圆满了的时候,突然一场大火把除宫洺、林萧外的所有人都烧死了。这场大火来得毫无缘由,不少人归结为郭敬明喜欢“虐”。当代青春流行文化狂欢的表面下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悲伤,这也一向被解读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真的如此吗?是不是有外人难解的况味?本该少年张狂时节的摧眉折腰,本该奋不顾身年纪的斤斤计较,本该不共戴天的仇敌,却要深深爱恋……做狗是有代价的。每当我想说些什么的时候,总想起一个学生在邮件里写给我的话:“当你们在指责我们这一代人精神荒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是谁把一个如此荒凉的世界留给我们的?”
(摘自《天涯》2015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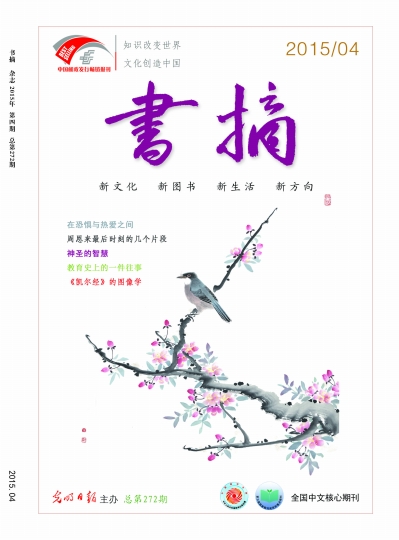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