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街口外大街19号——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门牌号。
熟悉北京的人一看便知,这门牌一定是多年前核定的。当初,师生们从教学区东门进出,东门确实开在新街口外大街。如今,东门早已弃置不用,取而代之的是气派的南门。而南门其实开在学院南路。
中国建筑理念中,面南背北为方正,一般来说南门是正门。重新启用南门,原因众多,我猜多少有点“必也正名乎”的意思在里头,只不过“正名”换成了“正门”。
1985年9月的一天,我身穿的确良衬衫,留着“叔叔阿姨头”(从前面看是叔叔,从后面看是阿姨),骑着自行车,后座驮着行李卷,前车把上挂着叮叮当当的洗漱用具,从师大东门进入校园。自此在这里度过四年光阴,见证了一些有意思的人和事。
80年代中期,是大学老师新老交替最轰轰烈烈的时段。七老八十的老先生们尚健在;三十出头的俊杰们正在跟着老先生们读研;四五十岁的中坚力量,虽然大多已是各自学科的顶尖高手,但论资排辈,还没有专职带研究生的权利,还在给本科生上大课。我入学时,钟敬文、陆宗达、李何林、黄药眠这批巨匠不光带研究生,偶尔也给本科生讲大课。我在这校园里上的前几节大课,授课者正是钟敬文、陆宗达两位先生,讲课内容是他们的治学之路。老先生亲自出马,是对新生的优待,旨在励志,这是学校欢迎新生的固定套路吧。
我们的主课老师,古汉语有许嘉璐等,现代汉语有李大魁、周同春、杨庆蕙(值得一提的是,杨老师曾亲炙师大老校长黎锦熙先生)等;古代文学方面有韩兆琦、邓魁英等;现代文学方面有郭志刚、杨占升、蓝棣之等;语言学有岑运强(语言学泰斗岑麒祥先生之子)。我们毕业后没两年,新老交替迈了个新台阶,这些人全都成了博导,本科生们很难亲聆教诲了。
年轻一辈,我们入学时,中国第一个鲁迅研究的博士王富仁刚从李何林老先生处出师,留校任教,代过我们现代文学史课,也给我们开选修课。王一川、刘晓波当时正在跟黄药眠先生读博士,在职读博,所以也给我们开课。
这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现在论来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不过我读书时不是好学生,不太和老师接触,只能讲讲印象较深的片段。
老一辈的,其他几位老先生平时极少见到。钟敬文先生喜欢散步,经常在校园撞见。冬天黑呢子大衣,呢质圆顶帽,春秋天则是灰布中式对襟衫,夏天一般就是白衬衫。腕子上吊着根手杖,走平路时好像不怎么用,总是做沉思状,但若有人上前请安,必笑咪咪微欠上身回礼。当时他已八十多岁,一个白发老先生悠然自得地在白杨树间散步,这是当时校园颇为迷人的一景。
中间一辈,许嘉璐老师的古汉语课是中文系学生的最爱,别的课迟到没关系,古汉语课别说迟到了,不早早去占座都没位置坐,因为有外系的学生来听。许先生讲课极幽默,经常引得学生哄堂大笑。还记得他在课上顺口讲过个段子,说他姓许,太太姓白,就有朋友戏称他们二位是许仙和白娘子。
蓝棣之老师身材略显纤弱,头发却硬硬地立着,不成型,一看就极有个性。他是新时期社科院第一届研究生,导师是唐弢。我们入学时,他还是个讲师,典型的青年教师气质,阳光、爽朗、叛逆。不过几个月后,他仿佛一夜之间苍老十岁,本来就有点少白头,至此几乎全白。后来得知,就在那年秋天,他最疼爱的儿子在一场电梯事故中不幸丧生,才十七八岁,刚刚考上大学。从此再见蓝老师,眼神深处,总有一股幽幽的悲凉,哪怕是在和学生们说笑时。
他是研究现代诗歌的,当时的研究课题是新月派。徐志摩、林徽因这些人的作品,在当时学界还未完全摆脱“格调低劣”的噩运,蓝老师已经开始用他一口“川普”满怀激情地颂扬,不吝惜任何美好的词汇,因此迅速得到学生们的拥戴。现代诗坛的各种文人逸事,也是蓝老师的长项,学生们无不听得兴头大起。蓝老师会从这些典故中总结一些道理,比如他说:男女恋爱初期,男人是女人的父亲;刚结婚时,男人是女人的丈夫;老夫老妻时,男人就成了女人的儿子。
蓝老师家里,经常坐满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学生,从早到晚。和我同寝室的一个同学一天深夜回来,脸上放着光,问他哪儿打了鸡血,答曰刚在蓝老师那儿长谈。那一夜,这位同学翻来覆去睡不着,神经病一样地反复念叨:蓝老师了不起。
还有一位诗人老师任洪渊,当时也是个讲师,也受到众多学生追捧。任老师研究当代文学,不过依我看,他对研究兴趣不大,为稻粮谋而已,他的兴趣在写诗。任老师在当代文学研究的课堂上,经常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当成研究对象,与他的粉丝们分享他对自己的“研究”。任老师当时新婚不久,妻子比他年轻很多。在任老师笔下,她叫FF。任老师那段时间的所有诗作,差不多都给我们当堂念过,题目、内容千变万化,永远不变的是,念完题目紧接的那句:献给FF。
王一川老师给我们开了一门选修课,文艺美学,主要讲海德格尔,那是他当时的研究重点。王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川大读的本科,北大读的硕士,师大读的博士,我们毕业前,他又远赴英国,在牛津大学读了伊格尔顿的博士后。学生们闲聊中说起王老师,都将之视为神童型学者,因为,他看着一张稚嫩的脸,讲起课来,竟然那么学识丰厚、魅力逼人。此刻我写至此处,脑海浮现出他一张少年般的脸庞,在讲台上不疾不徐轻柔地讲述着:“在茂密的林间,有一片空地……”
王老师因为面嫩差点儿吃了亏。他还在读博士,常到学生食堂吃饭。有次在食堂,几个人高马大的体育系学生乱加塞儿,王老师客气地告诫了一句,那几位兄弟看看他,骂骂咧咧地训斥他,哪来的新生啊,对学长什么口气啊!一边说着,开始露胳膊挽袖子。我排在队伍后边,见状赶紧上前警告那几位兄弟:放尊重点儿,这其实是位老师。
与钟敬文先生散步一景相映成趣,校园另有一景也很迷人。校长王梓坤经常骑着他那辆蓝色的二零坤式自行车,在校园穿行。精瘦的他,骑着那么小的车,就像一根竹竿在水平移动。单看他骑车转圜自如的样子,就算在那个精神重于物质的时代,也很难相信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北师大的校长。
80年代高校间流传一个顺口溜:苦清华,乐北大,要谈恋爱到师大。清华当时是纯理工院校,学生学业繁重;北大人自带一股天之骄子的自信,所以老乐呵呵的;师大呢,恋爱之风盛行。
也真是。我们刚入学没俩月,班里就迅速有三四对同学建立恋爱关系。毕业之后,全班120个人,不出本班有30人结成15对夫妻。我们毕业时,学校还管分配工作,可忙坏了那些成双成对的幸福人,分配原则是哪儿来回哪儿去,可结对儿时,并不会专挑老乡啊,就得往同一个城市调配。
那时的爱情,不如今天年轻人谈得这般奔放,绝大多数都主打羞涩牌。有对恋人,因为女生太腻,经常没骨头似地吊在男生肩膀上,还引起不少非议呢。既羞涩,就要扯一块遮羞布,这块布就是读书。
那时生活简单,没有网吧,没有酒吧,更没有夜店,街上连小饭馆都没几家,就算有,也不是穷学生惦记的,就没这风气。彼时所谓谈恋爱,一定离不开读书。常见模式是:一大早起,两人各挎着书包,饭厅碰头。吃完早餐奔教室,并肩坐在一起度过上午四节课。中午一起吃完饭,各自回寝室休息。下午在教室碰头,继续肩并肩度过两三节课。晚饭一起吃,吃完再奔教室,肩并肩地上自习。教室灭灯前,各回各宿舍,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枯燥吧?其实未必,这简单的程式里,无数柔情蜜意汩汩流淌。比如早晨男生起晚了,疯狂赶到饭厅门口,发现女生一脸娇嗔,手中手帕里捂着给男生买好的早餐:“这都几点啦!来不及啦,赶紧走!快吃,还热着呢。”比如教室里枯燥的四节课,女生起得太早,可以偷偷睡一觉,不必担心落课,男生正在身边奋笔疾书记笔记。比如午餐时,女生突然变戏法似地端来一盆最贵的大菜——红烧排骨,那是女生省吃俭用攒下的体己钱买的。对,那时候粮票尚未取消,菜金和饭票是分开的,男生饭量大,经常一到月底就大瓢底,这时女生的饭票就顶了大用场。如果还有富余,女生会找小贩用粮票换一两盒烟,悄悄塞在男生书包里,赢来一个小惊喜。再比如,晚自习不像上课那般正式,读书读疲了,恋人们会溜达到主席像前的小树林,钻进去找个长椅坐下,在夜色笼罩之下,羞涩地拥抱亲吻。而当他们拥抱亲吻的时候,他们身体的一侧,各有本书翻开着,那是他们出来时不自觉地拿上的道具,随时不离左右的道具……
当然不是所有同学都有幸找到意中人,孤男寡女们就把浓浓的荷尔蒙发泄到读书这事儿上。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好学生,他们任何时候都独来独往,奉课本和考试为神,努力创造好成绩,以抵消青春期的孤独——当然,这么说,和他们立志学业、志在千里并不矛盾。另一种情况是一群自命不凡的家伙,他们最不喜欢上课,但天天逃课躲在宿舍或是图书馆里,博览群书,而且专挑犄角旮旯的偏门书读,以求最广阔的视界,下次再有辩论时,他们口沫横飞,不把你侃晕绝不罢休。不过,那时的所谓偏门书,也不是今天这个概念,而是《梦的解析》之类的大俗书。
周末,恋人们纷纷打扮得漂漂亮亮,奔赴北太平庄、西单等处逛街,单身汉们会选择骑着车,把全北京的小书店逛个遍,不定在哪家旧书店,就能淘到一本心爱的书籍,拿在手中摩挲,那感觉不亚于面对美妙恋人。
2009年夏天,为了纪念毕业20周年,我们班七八十号人从四面八方赶到北京。在师大东门外一个餐厅大聚一场。夜深人静,各自使劲抑制那颗奔腾的心,趁着夜色,从师大新南门鱼贯走进我们青春的墓园。教二101还在,教七101还那样,主席像拆了,小树林变成了宽阔的广场……没人大声说话,都在各自细数在这个大院留下的点点滴滴。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营盘有些小变化,但营盘还是营盘,无数年轻人还在这里读书、恋爱、打架,像我们留下的影子;而我们,真如流水一样,流到东南西北的大地中去了。
(摘自《门牌号》,中信出版社出版,定价: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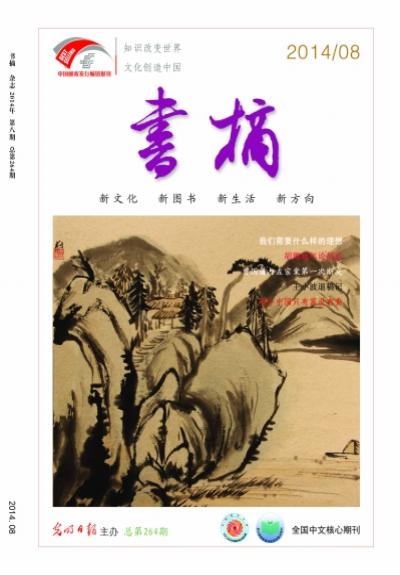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