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刘心武与著名学者张颐武共同探讨新时期下关于人文精神、宗教情怀以及理想的话题,观点深刻,富有启发性。
关于“人文精神”
张:最近以来,有关“人文精神”的话题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好像整个知识界都卷入了这个话题的争议。
如果从字面的修辞技巧来说,“人文精神”无疑是一个美妙的词。但“文革”时代大词好词也是满天飞,那些大词好词背后的东西却让人警惕。如果我们现在也不负责任地随心所欲地用一些“好”词,把它推销给普通人,其实也是一种语言的暴力。特别是这些大词背后所肯定的却是一种极端主义的思潮,那么其危害性就很大了。目前看来,“人文精神”的话语所肯定的却主要是一种神学的思潮。这个概念虽无比较明确的界定,但却是用来肯定一种“新神学”的,成了一种把极端主义的“新神学”以理论的方式合法化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语义混淆的方式为“新神学”辩护。它一方面采用了一个较宽的语义,把“人文精神”作为一个大而化之的好词,作为“精神文明”这样的概念的同义词来使人感到这种提倡几乎不可缺少;但在具体的表达方式上,却有极为浓厚的极端主义的色彩。
这种极端主义的色彩表现在对于当下文化的一种极端的否定性的描述之中。它们把最好的辞句用于歌颂一些有明确“神学”色彩和背景、充满对于世俗文化和普通人的“仇恨”的作家。而对其他人和当下文化的一般状况一笔抹杀。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精神”的表意策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将社会目前所面临的一些道德问题,一些容易与人们起共鸣的问题拿来为己所用,最后却推出了自己一套神学的解决办法。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做法。因为在当下语境下,社会转型造成的许多矛盾、问题中确实有相当严重的道德问题存在。这些以道德问题作为表象的问题,其形成的原因当然比较复杂,而其面向也相当多样和不确定。其中有社会的、心理的、全球性的以及道德的多种因素构成。但“人文精神”的话语却不是分析这些非常复杂的问题,而是把它归结为社会的“堕落”。“人文精神”的话语之所以能吸引一部分人的兴趣,主要就是因为这种对社会问题的简单而相当锐利的提问方式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它把问题变成了一个异常明快的二元对立,使问题极度地化约了。但其解决的方案却是以“人文精神”这样一个含义极度含混的词作为关键符码。我们把关注点非常明确地集中于这里,就会发现“人文精神”变成了一个类似气功中的“气”这样的十分神秘的、包含一切的东西。于是,你发现一切均十分神秘含混,但留下的唯一明确的指向是一种“虔信”的思路,一种为“神学”留下的空间。最后我们才发现,在这种异常美妙的人文精神之中,唯有一种“新神学”的作家才是值得肯定的,只有他们才有理想,才崇高,才能为社会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道德问题,指供一个明决干脆、快刀斩乱麻式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新神学”的信仰与“人文精神”有很明显的西方倾向的思路是不太能够完全沟通的。但它们用一个“理想”、“崇高”这样的大词“接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在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否定上完全一致,但却在其他方面并不完全一致的一个较大的思潮。我想它对目前中国文化发展产生的一些影响还是值得我们十分关注,并加以分析的。
刘:我的感觉,一个人对于时代的描述,有权根据他自己的主观想法来进行。我们当然应该允许别人的想法和我们不同。如王晓明等人认为目前的文化状态是“旷野”,是“废墟”。我不能说他的感受就错了,我的感受就对了,我只能说我的感受和他们的不同。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确已成长成一片树林,一片茂密的森林。这片森林是在原来“文革”时代的荒芜的“旷野”上长起来的,而且长起来的时间不是太长,在这个生长的过程中它的不平衡状态也还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一些地方是“疯长”,有一些地方也还有没有长起来的。但你说它是“旷野”、“废墟”恐怕不尽准确。
再说到道德的问题,我也要表达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似乎也不应该把我们看不惯的一切问题都视为是道德问题。这种意识同样也是很有缺点的,因为道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不断变化的。你很难用你经常讲的一套来衡量社会的一切。像诸如还没有合法婚姻手续就同居,这恐怕还是个个人私生活的选择的问题;再像结婚后不生孩子,也是个人选择的问题,都还提不到道德层面上。像作家要稿费,一看稿费发得不合乎规定的标准或双方的约定,就和出版社理论一下。这在过去显然是道德不够高尚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却是注重作者自身的权益,是自尊和人格的表现,国家也特别制定了版权法,保障作者的利益。这就是道德观念转变的一个标志。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民间存在总体上看还是良性的,而且它的空间正在展拓。我觉得从总体上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树林。有一些很怪的植物或是害虫,但它很有机会发展成一片非常美妙的森林。所以我对于当下的文化状况是持一种亲和态度的。
而对出现的问题,许多论者提出“人文精神”的命题,有些朋友是把它和“精神文明”画等号的。如果是这样一个提法,那就无需乎讨论了。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像“人文精神”这么一个概念它装不下丰富的精神文明的内容。像爱国主义,它显然就是一个独立的概念,你很难说它就是“人文精神”的一部分。这么说从概念、逻辑上也不太说得过去。
人们如果这么任意用一个词来大而化之地谈问题,不但价值不大,而且也会有许多问题出现。他们有一点意见却是很值得讨论的。他们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终极关怀”,这我认为是极有可议之处的。对我个人来说,我是认为“终极关怀”与“人文精神”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的概念。“人文精神”恰恰是一种相当世俗的关切。而“终极关怀”则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追求,是超俗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关怀。一个普通的人,他没有什么哲理的思索,也缺少一点深度的探索精神,但这也并不妨碍他对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不妨碍他在家庭和社会中承担的责任等等。
所以,我想我们面对今天相当复杂的文化转型期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采取一种更为实际的分析的态度、一种平和的立场恐怕是非常必要的。
神学话语兴起的反思
张:你刚才的分析是相当准确的。特别是对于“人文精神”的分析,非常有趣,而且的确抓住了关键的问题。现在看来,还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最近在中国大陆出现的一股神学的潮流。这种潮流近来作为一种社会文化选择的影响很大,它给不少人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的种种问题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方案。这种宗教的情怀与“人文精神”的表达有非常接近的地方,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很明确的宗教的背景。我觉得这也形成了一个“新神学”的思潮。
从现在看来,“新神学”的冲击力在于它相当尖刻地提出了当代生活的缺少信仰的问题。它要提供一个终极的“拯救”,要拯救当代人,要毕其功于一役,一下子解决当代人的所有问题。要用一种彻底的精神拯救把当代超越,把今天超越,让人走向一种永恒的目标。所以他们都很强烈地反世俗,反对当代的社会进程。这种思路和“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有很大的差别。“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确实追求伟大,但他们所追求的伟大却有一个十分具体的世俗的目标,有相当世俗的目标,就是让人们过上更好的日子,追求更美妙的生活,就像你所说的那种“人文关怀”一样。但目前经历了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之后,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彻底反世俗的宗教的信仰的思潮,的确这是很引人注目的事件。这种思潮提出了许多值得引起我们关注深思的问题。
首先,它使得当代社会的许多征候被一下子突出了出来。其次,它所提出的这种神学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也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它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据美国学者斯达克等人的统计,全世界大约百分之六十的宗教团体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来的。人类生活面对的种种问题难以被很好解释,找不到有理性的阐发之时,就给宗教留下了巨大的空缺。而当代的文化语境中那种无意义的痛苦,那种难以为日常生活赋予充分的合法的理由和意义的痛苦还是相当沉重的。科技的发达,理论及人文科学的发展,人类登上月球的奇迹等等都不能使神学的影响力降低。而且当前的宗教生活由于经济的发展也远比传统的宗教生活更有实力,更能够有经济上很强的保障。从西方来看,目前的宗教组织、团体往往都非常有钱。因此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就是20世纪以来人类的生活越来越世俗化,而同时对这种世俗化的反抗也更加强烈。这些宗教潮流各有各的走向。有不少是利于人们修身,帮助人的,但也有一些是诉诸一种十分激烈的反社会、反体制的活动。这些教派都是承诺改变世界,给世界好的东西,彻底拯救。如果这种彻底拯救始终不来,就要诉诸行动,就进行社会的冒险和恐怖的活动。因为这些新兴的宗教一定要宣布我是唯一的,我是最正确的,我发觉了拯救世界的方案等等,那么这种新兴宗教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也是有它的社会和文化的原因的。
那么对中国来说,目前的社会进程中出现这样一种具有某种极端性的宗教诉求是不奇怪的。它还不能说是一种真正的教派活动,还主要是某些特定的人群的极端诉求。这种诉求也已经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我觉得这也有一些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一个神圣的时代终结之后,人们进入了一个世俗的生活之中,原来虽然生活很贫乏单调,但生活的目标依旧极为明确,日常生活处于一种被赋予了很大的神圣含义的状况之下。我小时候随父母到干校,有一次吃饭吃饺子,就有连长讲话说吃完饺子,养足精神反击帝修反。这一类的表述都是把一些很世俗的活动赋予很大的含义,使它变得非常神圣。当今中国社会的市场化的转型,极为强烈地凸现了世俗化的追求。世俗化的日常生活的物质改善一直是社会的一个主要的目标,这当然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新神学”突然把一种看起来很不得了的意义给予人们,这当然是使得—部分人感到很迷醉的一个原因。世俗的人生追求很难完全满足人们的心理的需要,特别是一些中国社会转型中被抛在急剧变化的进程之外的人更容易与之产生共鸣。
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有很大的危险性,很值得我们去警惕,因为它是很独断、很极端的社会思潮。用这个教派的原则和立场否定社会上与自己有差异的其他思潮和观念的存在的权利,我觉得构成了文化冒险主义,不能不与之争论和探讨。还有如将“大批大批的中国人”说成是“已经准备好‘从肉体到情感’地出卖了”之类的意见都是很可怕的。这是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的文化冒险。因为面对今天纷纭复杂的社会状况提不出有力的解释,只凭着一种迷狂就去寻找结论,的确会挑动社会的敌意。比如呼吁“清洁”的人,他就一定要把其视为不洁的人加以清理,这是相当危险的。在学理方面,这种思路也是一种独断的思想,一种独白式的写作。从这两个方面上看来,这种“新神学”的追求必然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无论在社会实践还是学理上,它的毛病与局限都是非常清楚。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想
张:一个与宗教情怀有关的话题,就是如何去思考“理想”,这样一个比较广阔的概念。 “理想”这个词最近以来比较多地被用来指称诸如“人文精神”或是一种“新神学”的信仰。目前像“人文精神”或是宗教的“新神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也就是它们都是进入媒体的,都是大众传媒的新宠。在媒体中很复杂的学理性的内容,很多逻辑推理或论证的过程都被省略掉了。媒体的确只能提供一种“形象”,一种感性色彩较强的东西。媒体在采访中或者说报纸上很短的文章都有一个很明显特点,就是论证相当简单明快,结论相当单向、简单。往往只有一个结论,而没有论证,且这个结论又是很直接的,很明确的,非此即彼的。这里就有一些来自媒体的简单化的策略。这种策略是比如你对“人文精神”或是“新神学”从学理层面上提出一些疑问或批评,那么对你的观点在学理上是否有说服力往往并不重视,对你的论证和比较复杂一点的结论也不感兴趣,往往是认定你不要理想,放弃理想。这样问题就很严重了。但现在的麻烦事在于,究竟有谁宣称自己不要理想,宣称自己主张堕落?王蒙先生的《躲避崇高》一文,好像一直被认为是不要理想的一篇文章,你的《直面俗世》也被人这么看了。这的确是相当可笑的。
理想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把理想变成一个缥缈的玄学的概念,就太抽象以致难以把握。理想的诉求非常需要具体化、清晰化。否则谁都可以随意使用,任意赋予它怎样的意思都行的话,恐怕也就失掉了任何讨论的意义了。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理想”—词有两个意思,一是对未来事物的想象和希望,二是符合希望的,使人满意的意思。这两个意思当然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考虑,有不同的选择的。
刘:我觉得“理想”这件事实际上是相当简单的。实际上是人对于现实满意不满意。人们一般是不满意的,就要创造出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来。这就是理想的存在。文学天然就是“苦闷的象征”,都是对社会生活有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文学作品或是对现实的反思,或是对于现实的补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绝大多数的作家都是有理想的,只是其深度、高度或面向有所不同而已。从历史上看,也的确有看不出比较明确的理想的书。但这样的例子不是很多,特别是像《金瓶梅》这样看不出非常明确的理想,又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的书是不多的。你像有一位周瘦鹃老先生,专写花花草草……
张:这是位鸳鸯蝴蝶派的老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就专写花草了……
刘:他的作品好像看不出什么理想,但通过对自然的发现,也寄寓了人类的一种希望,其实也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你也不能说他的作品就没有理想。因此理想对于作家来说,总是很明媚存在的。你说王朔的小说没有理想?只是他的理想可能与你的有差别,不尽一致而已,他的小说里也依然是有潜在的理想的。理想的存在,我作为—个个体生命来说,总是有一种向未来的预想预测,有我的期望值。这些都可以归入理想的范畴。我觉得这里要注意的只有两点。一是理想的追求不能脱离我们的生活实践。提倡一种与现实无关的理想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一种压抑普通人的正当的物质追求的理想,也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理想必须是与当下的人们有关的,与他们的生活境遇有关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强加的离人们很远的东西。其次,理想不能是一种独断的思路,不是一种唯一的、不可怀疑的正确的东西。它应该也是各种各样的,既有不同的层次,也有不同的面向。要求全人类只有一种理想,那么这种要求的危险性是很大的。恐怕有关理想的分歧实际上是:要一种与人们相对抗、对人们充满仇恨和蔑视的理想呢,还是要一种能和人们沟通的、交流的理想呢?是孤傲地斥责一切,认为唯有我发现了真理呢,还是在生活实践中寻找具体的目标呢?这恐怕是最重要的问题。
张:你这个说法的确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理想的确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我们更应该关切的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理想,这些理想是不是与我们有关,是不是帮助我们向前走的。如果不是这样的理想,我们就必须提出我们的反思与参照。
摘自《跨世纪的文化瞭望:刘心武、张颐武对谈录》,漓江出版社2014年5月版,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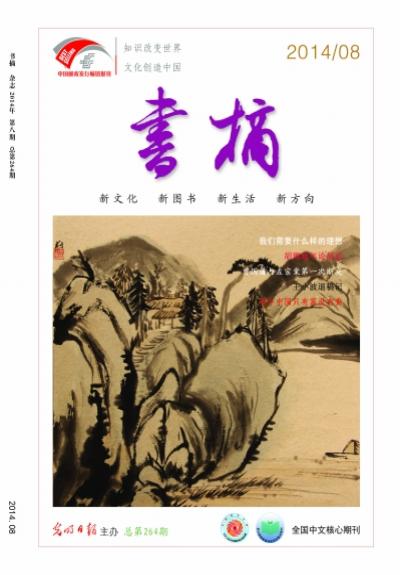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