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绵的追问与回忆之间,阎连科与梁鸿展开了精彩的对谈。作家个人的历史回眸、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前景、民众命运何去何从,一幅幅可感的画面重新回现,多少悲欢离合、穷形尽相都不脱厚实的悲悯。
命运的伏笔
梁:最初写小说的动机是什么?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吗?
阎:根本不是。是有一天,我忽然看到张抗抗的一部小说《分界线》,在这部小说的后记里,写道因为她写了这部小说而从黑龙江农场调到省会哈尔滨工作了,当时看完震动特别大,忽然发现写小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于是,就开始写小说了。
梁:那时你多大?
阎:十七岁,读高二。
梁:写了多长?
阎:二十多万字,是所谓的长篇。
梁:写了多长时间?是什么内容?
阎:有两年多吧,内容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一类。
梁:后来这部小说的命运怎么样?
阎:小说的命运可想而知,但它还是给我的命运埋下了伏笔。没考上大学,1978年就当兵去了。我一直说我的命运不错,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在新兵连里干部们看我的钢笔字还说得过去,就让我去出黑板报,黑板报快出完时,正好教导员转了过来,看到我写的粉笔字横平竖直,和顺口溜一样的诗也还押韵,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就问我写什么东西不写,我就说写过小说,他听后吃了一惊,说抓紧寄过来给他看看,我就让家里把那一大堆东西寄给他看。后来,新兵连结束的时候,教导员就让我在连队搞报道。接着就是中越战争。在这期间,武汉军区开了一个小说创作学习班,教导员就推荐我去了。
梁:那你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什么?
阎:叫《天麻的故事》,写的是一个战士为了入党送给指导员一斤天麻,指导员巧妙地把它退了回去,又没伤战士的自尊心,并且还讲了许多无私的革命道理。有三千来字,寄给原武汉军区的《战斗报》,就发了。时间是1979年的下半年,我记得很清楚,后来收到了8块钱的稿费,拿出4块钱在班里请了客。
梁:当时什么感觉?
阎:不敢相信。见到报纸和第一次收到情书一样,一个人跑到厕所蹲下来,偷偷地读了一遍。
梁:命运就从此发生变化了?
阎:开始发生变化了。那时候,军队对通讯报道特别重视,全军有一个任务,就是新闻报道要“消灭空白连”。每一连队每年必须见报一篇,每个营都有专职报道员,因此我被抽到营里,替每个连队写。当时有规定,《解放军报》见报一篇,记一个三等功,五篇省级以上累计一个三等功。于是,“七一”快来了,我就给这个连队写一篇押韵的“散文诗”歌颂歌颂党;“八一”将到了,就替那个连队写几句诗,或者“战士格言”什么的,歌颂歌颂建军节;无节无日了,就写一些读者来信什么的。
梁:都能见报吗?
阎:写十封读者来信还能不见一封吗?
梁:也就立功了,提干了?
阎:立功了,入党了,退伍了。
梁:为什么?
阎:我刚当兵的时候,只要打仗立过功的战士全都提了干,但是,后来干部太多,部队下了一个紧急通知,不再直接从战士中间提干了,这就只有退伍了。三年服役期满后,就在1981年年底,办了退伍手续,拿着117块钱的退伍费、120斤粮票,托运行李回家了。
可就在这时候,在我上火车准备回家时,在火车要开的前几分钟,突然,站台上飞驰过来一辆北京吉普,我们团长从吉普车上下来,大声喊着:“阎连科在哪儿?阎连科在哪儿?”
我从火车上慌慌张张下来,团长说,现在有一个提干指标,想提,你就留下,不想提,你就走。当时我就傻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团长说你回家也可以,和父母商量商量,半个月内如果你人不回来,这个指标就作废,回来就提干。这样我就又在火车启动前上了火车。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提干指标是武汉军区在全军业余会演中拿了第一名,总政首长接见演出队时,军区文化部向首长汇报,说这一批文化骨干大部分演出完后脱下军装就要转业回家了,于是,总政就给武汉军区特批了二十多个文化骨干提干指标。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发了几篇小说,写过独幕话剧,也算个文化骨干。我回家待了半个月,卖了一头猪,回来还掉退伍费,参加了一个文化骨干培训班,就终于提干了。
梁:终于柳暗花明了。
阎:是因为爱好文学埋下的伏笔把命运改变了。
土地构筑的心灵
梁:你从来都不说自己是一名作家,而总是说自己是一个农民。为什么要这样说?你觉得是真情还是矫情?
阎:无所谓真情,也无所谓矫情。我之所以直到今天还说自己是农民,大约有两层含义:一是我全部的亲人,今天几乎都还在土地上耕作,几乎都靠着土地生存;二是我虽然以写作为生,是一个专业作家,但是,不仅我的作品几乎写的都是农村、农民,而且我的日常生活、一言一行都非常农民化。
梁:你不介意人家说你是农民作家吧?
阎:不。我介意。
梁:为什么?
阎:把作家分为农民作家、工人作家、城市作家、军旅作家,这不光是中国唯成分论的延伸,而且有碍于一个人的写作。作家就是作家,农民就是农民;前者劳动的结果是作品,后者劳动的结果是粮食;一种是精神范畴,一种是实物范畴。
梁:你既然不愿意别人说你是农民作家,那为什么又愿意称自己是农民?这不是矛盾吗?
阎:我说我是农民,是在呈现一种我内在的真实。巴尔扎克说要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努力,而我刚刚离开农村、土地才二十来年,我怎么敢说我就不是农民了呢?
梁:你把农民这个概念复杂化了。简单说,农民就是种地人,就是庄稼人,可现在你已经不是种地的人、庄稼人了。
阎:还有一种农民,他们不种地,但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心灵,都是由土地构成的,他们的表面似乎已经不是农民,但他们的本质还是农民。
梁:比如你?
阎:还有你。你虽然是一个博士,可你是一手握着锄头,一手握着钢笔,完成了青少年的学业。毫无疑问,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庄稼人了,已经丢掉了锄头、镰刀、铁镐等农具,可你的心灵世界是由土地构筑而成。那块土地下掩埋着你的上一辈、上几辈的亲人。还有,今天、现在,你许许多多的亲人,都在那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就决定了你只能是农民,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人。
写作是一种日子
梁:我曾经问过你写《写作是一种日子》这篇短文时的生命感受,现在我想问的是,你是如何看待你的写作和生活的?
阎:就我而言,写作是一回事,现实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说它们有联系的话,那么就是现实生活对我写作的支持,犹如流水对土壤的支持一样。我在那篇短文中已经说过,我在生活中要写作,就是要过日子,日出日落地对写作的努力和继续就像农民不种地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就要挨饿一样的道理。不写作便使人觉得恐慌、心烦、没有着落,像吃了上一顿饭找不到下一顿的米一样。重要的是我要能把过日子化成写作,一日一日地写下去,如此,就够了,满足了。现实生活中过好日子固然是一种愿望,但过日子才是根本。不会过日子,就没有好的生活,我就是一天一天地生活,一点一点地写作。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梁:但是,我总觉得你在其中流露出了特别沉重的东西,或者说你这篇短文的基调并不那么乐观,是不是与你的身体不好有关系?或者目前你正处于某种写作的困境?
阎:身体不好的确会影响写作,许多时候,你会明显地感觉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又看到自己所写的东西迟早都会成为垃圾,不要说百年之后,就是十年、几年之后,就会一文不值、什么也不是。明明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又不得不继续去写,这就会使人非常无奈,像砍月桂树,像西西弗神话中不断往山上滚动的石头。
梁:你感觉现在你所面临的最大痛苦是什么?
阎: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事情是,记忆力在衰退,眼也开始老花,这是一种衰老,非常明显,说起来好像有点作秀,但又真是这样。任何书看完就忘,有时候根本看不进去。
梁:为什么看不进去?除了身体不好外,是不是与没有耐心有关?
阎:耐心不是看书的方法。看不进去的书,你强迫自己看完了,不会有什么收获。比如有些书,看几遍都不能看完,但又不能不硬着头皮看。就像我说的,一本好书和作家之间必须拥有契机才能碰撞和沟通。
梁:现在你是不是很少看书?
阎:翻得很多,但都是蜻蜓点水,这是非常致命的。
梁:你现在会不会觉得看书已经不能扩展你的思路了?
阎:说不准。但是有一点是,如果一本书能让人一字不落地看完,肯定是对你有非常大的震撼力,能真正扩展你的思路。
梁:你曾经提到“土地文化”的说法,并且认为“只有心灵中的故土和文化,才能使作品有弥漫的雾气,才能使作品持久地有一种沉甸甸、湿漉漉的感觉……”,就这些话而言,能感觉出你对作家心中的故乡看得非常重,你认为你所说的“土地文化”和“地域文化”有什么区别?
阎:“土地文化”不是地域文化,但土地文化包含了地域文化。我不赞成“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说法,这对小说创作尤其不合适。再土、再民族,你能土过民族、土过“山药蛋”吗?山药蛋派有一些优秀的作家,但我们不能说他们就是世界级的大作家,不能说他们的作品和托翁的作品一样,都是世界文化的财富。“二人转”、剪纸是极其民族化的了,但它是世界的还是我们家门口儿的?
梁:我从你的作品中,能读出你对“土地”的一种信仰,并且你的作品也始终浸染在神圣而又沉重的土地中。
阎:我没有想过文学与信仰这个问题,也没想过土地与信仰的关系,我只是按我的想法不停地去写就是了。文学与土地都不能成为你的信仰,这是非常痛苦的,信仰对精神来说是非常实在的,有信仰的人远比我们生活得幸福。而我们活着与活着的写作,最终都只能是一种虚无。
窘境中的河南人
梁:我们现在来谈谈河南人吧。
阎:为什么?
梁:因为最近几年,国内对河南人的歧视似乎越来越严重,一句“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传遍大江南北,而在实际生活中河南人被无端歧视的现象也非常明显。但是,平心而论,我所知道的、所感觉的河南人真的都是非常好的,忠厚善良,甚至有些羞涩,无论是生活在什么阶层,都非常热情、朴素,当然,也不排除河南人有犯罪、造假的现象,但我只能说,这是中国的国情,而不是河南独有的现象,为什么就单单把河南挑出来成为调侃的对象?
阎:河南人有一个亿,按比例算,出一些素质不高的人也是正常的。中国仿佛是一个需要有内部敌人的民族,内部没有敌人,似乎民族就没有了方向。几十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养成了在斗争中发展的习性,你不能让它一下没了斗争方向,那样人们的生活、工作和业余活动会失去许多意义。现在,大家都为钱奋斗——而不是斗争——感到十分疲劳时,是需要有一个“敌人”来延续他们“斗争的习性”,从而来缓解他们“奋斗的疲劳”,而河南人,不过是充当了这个角色罢了,用不着大惊小怪。
梁:情况的确是这样,这是中国国民最大的劣根性,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把注意力转移到别人身上,以摆脱自己的责任,然后,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可是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就选中了河南?
阎: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曾成为中国人谈论的对象。那时候,关于温州的话题特别多,比如造假等等。现在温州经济发达了,也走上了正轨,反而成为了人们羡慕、赞美的对象。而中国西部,还没有真正开始发展,还没有真正处于发展期,所以人们不会去议论它、讥笑它、调侃它。而河南,地处中原,又正处在这样一个发展期,被“选择”我想是正常的。问题是,河南为什么发展期的时间这么久,这么长时间发展不起来,这才是河南人应该真正思考的。如果河南三年五年就发展起来了,它就不会被人非议、调侃了。
梁:换句话说,因为河南正处在一个发展期,“枪打出头鸟”,因此成为攻击的对象也是很正常的。另外,我觉得这也与河南所处的传统文化位置有很大关系。河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承载传统文化最多,也最容易藏污纳垢。一旦要发展,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就开始起作用,成为一种巨大的阻力。
阎:对。要发展你又发展不起来,如果干脆停滞不前,可能也就不会遭受这么多的非议。但宁可遭人非议,也还是要发展的好。
梁:其实,这也展现了河南人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被非议恰恰说明了河南人在积极寻求出路。在这一寻找过程中,必然有许多缺点被放大和突出,成为众矢之的。但这并不是坏事,在被嘲笑的同时,也提醒了自己以后要改正。
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也的确是事实。在这夹缝中间、断层中间,要么你不发展,要么你已经发展起来,人们都不会说你,现在刚好在这两者中间,人们必然会说你。比如说河南巩县,原来也是造假比较厉害,但现在走上正轨之后,法制化了,反而成了经济发达地区,反而成了典型与榜样。
梁:问题是,现在这种情形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明显的地域歧视,包括对河南人的整体人格的歧视,河南人成为中国人中的二等公民,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的子孙将带着这种烙印生活。
阎:这种情况应该不会是长久的,发展时期的资本积累阶段,人格与道德作出牺牲是必然的。
梁:但是,作为河南人,其实不应该只去反驳,或通过翻出河南历史上有什么光辉事迹和名胜古迹一味地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是应该趁此机会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检视自身的毛病,以便真正得到发展。
(摘自《巫婆的红筷子:阎连科、梁鸿对谈录》,漓江出版社2014年4月版,定价:3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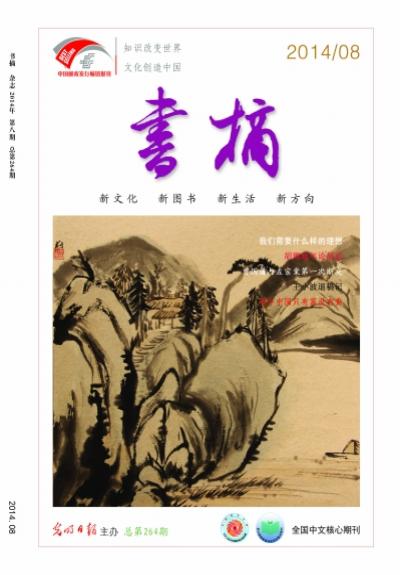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