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这样的国家,一个大作家的逝世,既不能盖棺定论,亦非入土为安,很可能还有另一段路程要走。说不定什么时候,总统一道法令下来,他被从基地翻出,以最隆重的仪式,迁葬到国庙“先贤祠”。先贤祠已经安葬了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马尔罗五位作家。很快,《三剑客》的作者大仲马将要跟他们会合,成为进入先贤祠的第六位作家。他跟雨果同一墓室,两位同年出生,生前来往密切的朋友,在他们诞辰二百周年的时候,成了永久的邻居。
先贤祠也像诺贝尔奖,绝大多数出类拔萃的作家和大德大贤的人被摒在门外。要是有人问,为什么蒙田、笛卡儿、狄德罗和巴尔扎克,或者被公认为拿破仑之后法国最伟大的人物戴高乐,都没有进入国庙?这可要问法国人。如果你征求别人的意见,每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人选,从拉辛到夏多布里昂、普鲁斯特,直到蓝波、柯列特,都有人提议,理由都很堂皇。现在大仲马被送进这个伟人的大家庭,大家同样会问一下居于什么理由,为他的文学成就?为他的传奇人生?
大仲马拥有一切成为传奇人物的条件。“我是一个黑人与白人的杂种,父亲是个黑人,祖父是个猴子。你的家族停下脚步的地方,我的家族才在那里开始。”他祖父原是侯爵,隐居在圣多米尼克岛,即现在的海地岛。这位侯爵跟一位芳名马丽·赛瑟特·仲马的解放了的黑女奴,养了四个孩子。当他因破产返回法国时,为支付旅费而将四个孩子当奴隶卖掉。四年之后,因为内疚才将长子赎回,他就是大仲马的父亲。这位长子返回法国后,发现他那个无良的父亲并不贫困,而是过着奢侈的生活。这位黑白混血儿嘴大唇厚,身材彪悍,力气过人,后来他选择军人作为职业,路子是走对了。入伍后,他从“皇后龙骑兵”的一名普通士兵开始,逐步晋升为将军。由于他的思想过于共和,以致与拿破仑意见相左,曾经入狱两年。得病后拿破仑让他退休返回故乡,生活拮据,大仲马三岁时他就去世了。后来这位将军的儿子挥动笔杆,就像他父亲当年挥剑驰骋沙场,于是我们就有《三剑客》、《基督山伯爵》和《玛戈皇后》等作品。他对黑奴祖母情有独钟,采用了她的姓氏仲马,这就是大仲马名字的来源。
大仲马一生写了多少部作品?大概三百一十部上下。但你多算或少算十来部,全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他比作家还要作家,比戏剧家还要戏剧家,他所创造的是他的神话。政治上像雨果,是个共和分子,参加过加里波第领导的意大利独立运动,乘着他的私人游艇“爱玛”号,到马赛为独立军购买武器。他在那不勒斯皇宫生活了五年,被加里波第任命为庞贝古城的考古挖掘总监;他在法国也参与政治,多次竞选议员;为推翻查理十世,他在街头跟造反派一起打枪;1851年流亡到布鲁塞尔,既为躲债,也因为反对拿破仑三世称帝;他鼓吹共和思想,先后办过《自由》、《人民报》、《新法兰西》、《独立》等报纸;他在俄罗斯、高加索、瑞士、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旅行,掀起了读者对他和他的作品的热忱。有一回他到莫斯科举行作品研讨会,他的作品因而在俄罗斯销售了四千三百万册。他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排斥异端。可见他文学创作以外,也参加社会活动,这点跟雨果相似。但是,雨果生前一切成就皆被认可,已经成为传奇人物。而大仲马呢?尽管生前为广大读者接受,作品畅销,却得不到文学界和学院派的认可,评论界不把他的著作归入真正的文学作品之列;政治上则被认为行为过激,不够成熟。每次竞选议员,均以失败告终,法国人不想他当议员;他希望进入法兰西学院,但终其生被摒弃在门外。那么,大仲马逝世一百三十多年以来,是走过了怎样一条道路,才抵达先贤祠这个身后的荣誉的?
一百三十多年来,从巴黎到莫斯科,到伦敦、纽约、北京、东京,都在阅读大仲马,谈论大仲马。为什么?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抵挡学院派和评论界对它长久以来的轻视?为什么大仲马直到今天才找回他生前应有的位置?据说很多孩子从九岁开始就阅读大仲马,达达尼昂、爱德蒙·当泰斯等人物伴着孩子们度过童年。当他们不再天真无邪,又帮助他们找回失去的童年和童年时代的梦想。《三剑客》、《基督山伯爵》等,使一代又一代读者产生兴趣,被一代又一代人一读再读,总带着同样的热忱,同样的梦想,因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知己知彼,亲密无间;他的作品只给人娱乐和精神享受,无意给人教训,只作独具慧眼的见证。故事中的文学、历史和冒险浑然一体,使人迷醉;一个古老而智慧,充满历史和记忆的欧洲使人流连忘返。读者被作品中的美梦、激情和异想天开带引着,被基督山伯爵这个时或慈悲为怀,时或满怀复仇欲望,相貌却神龙不见首尾的神秘人物吸引着。罪有应得,好心好报,有哪一位读者不感到满足?他们不但体验到阅读的乐趣,还从中获得知识,获得对事物的各种体验。阅读大仲马,永远不会感到枯燥。都说一旦接触到大仲马,就像染上某种美妙的疾病,永不痊愈。作者笔下的华丽世界,对19世纪上半叶巴黎的描写,一些华宅内部的奢侈浮华,我们今天看来还觉得新奇。作者对环境气氛的营造也特别出色,无论华宅、乡村客栈,或豪华舞会的情景,都能轻易地将读者带进惟妙惟肖的境界。《三剑客》、《基督山伯爵》、《二十年后》、《玛戈皇后》等几部作品,使拿破仑第三的共和国时代沉沉入梦,也使世界各地的读者,做一个遥远而甜蜜的法兰西美梦。随着时代的进展,各地大小银幕,都被他的故事丰富了。有多少个导演改编过他的《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为搭救危难中的皇后,为将价值连城的首饰及时送回国,达达尼昂跑了多少公里的胶卷?嘉芙莲丹露二十五岁就扮演奥地利皇后安娜,先后有过多少绮年玉貌的女星扮演过这个角色?电影这个第七艺术,没有了大仲马的作品将会怎样?《三剑客》早在1903年已经拍成电影,直到现在,总不时出现新版本。由法国人导演的电影《三剑客》,在强势的好莱坞面前,也曾经在美国风靡一时。
大仲马的作品恒读恒新,在世界各地不断被翻印。百多年来如此畅销的作品,评论界又怎能够只责怪它们结构松散,或流于通俗呢?大作家的手笔都比较自然、平淡、淳朴,像呼吸般顺畅自然,只求语言运用的准确有力,以及游刃有余。由于他是小说家兼戏剧家,小说中的对话特别精彩。雨果一早就以超时代的眼光,给予他极高的评价。1872年大仲马逝世,静悄悄地在维利耶·柯特烈村下葬时,雨果写信给小仲马说:“这个世纪没有一个人的声望能超越大仲马,他的成功比成功更甚,这是一连串的胜利,具有军号式的响亮。大仲马的名字已经超出了法兰西,他是欧洲的,甚至超出了欧洲,他属于全世界。”
雨果逝世时,法国举行了空前隆重的国葬,直接送入先贤祠。但大仲马逝世时,由于普法战争,也因为大家对他认识不足,葬礼非常简单。这两位名家碰在一块时,有点势不两立。但现实生活中,他们从年轻时代开始,已经结下了不解的友谊。1851年,大仲马流亡布鲁塞尔,雨果曾经去拜访他;1857年,雨果流亡格恩济岛,大仲马也亲临小岛拜访。雨果漫长的流亡岁月中,大家鱼雁相通。1865年,雨果给大仲马写信说:“一眨眼间过了三十五年。在我们的友谊中,不曾有过任何纷争,心里没有一点乌云。我写信给你,是为再次接通两颗心之间的电线。这条电线永远不该生锈,不该松弛。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力能将它毁坏。”雨果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相信不会想到他俩诞生二百周年的时候,会在国庙先贤祠成为永远的邻居吧!
先贤祠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进入,戴高乐就有言在先,要与家人永远葬在一起。有些伟人进入先贤祠,还不是他们最后的旅程。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米拉波子爵是第一个进入先贤祠的人,后来发现他跟敌人以及皇后马丽·安朵涅特暗中勾结,而被迁移出去;“人民之友”马拉,只在里面留了几个月,当他的朋友在政治上失势,他的遗骸马上被驱逐,送回到家族墓地上。目前在里面的卢梭,也经常被大家指责太革命,是个害人精;而左拉呢,又太过挑衅,为一个犹太人费太多唇舌。大仲马不妨碍任何人,只给大家带来快乐,所有人都愿意接受他,有谁不向他笔下的剑客致意呢?政治上当年不为人理解,身处现代的人也就理解了,也就是说,时代赶上来了。他曾经为反对种族主义被指责,如今反而成为一种时尚。他本人不就是一个白人贵族和一个黑人奴隶的后裔么?这个黑奴的后人还成了法国的大作家。这个作家以他的作品为法国制造了神话,他自己也从现实进入神话。
谈到自己的文学作品,大仲马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这样我会少死一些。坟墓让我死去,但书籍让我继续生存。一百年,二百年,一千年后,当风俗,习惯,语言,甚至种族,一切都改变了,只要还有我幸存的一本书,我本人就可以存活其中,就像一艘轮船和它的乘客沉没于大西洋,还找到一个在木板上死里逃生的人。”
(摘自《与书偕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月版,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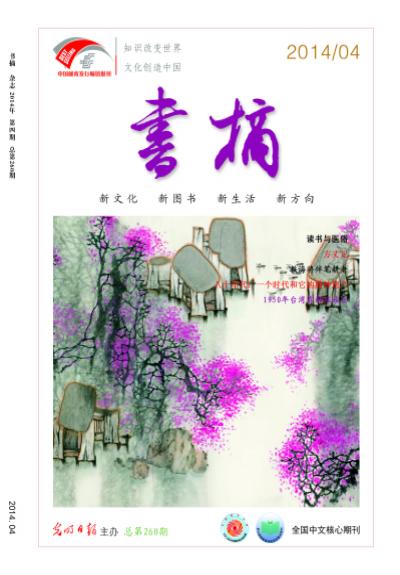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