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媒体多年,接触了很多文化名人,有的只见一次面,就亲切无比;有的见了若干次面,也很难走近。扬之水,属于前者。她,娴静,优雅,谦和,本色不造作。第一次见面,她指着身边笑眯眯的男士说,我家长。此后,“家长”成了我们大家的“家长”,在深圳,在北京,在全国各地。只要有扬之水的踪迹,就必定有“家长”陪伴的身影。“家长”带着我们去海鲜酒楼吃饭,陪着我们在东总布胡同参观,与我们一起听扬之水关于名物的讲座……我们习惯了“家长”的在场。
扬之水曾如此描述她家的庭院:“今日台历上录的是一首苏轼诗:倚竹佳人翠袖长,天寒犹着薄衣裳。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时世妆。下楼,蓦见庭院花畦中几丛芍药开得正艳。狂风撕掳着它的‘薄衣裳’,却仍自一番‘风流时世妆’。原来这几日正是芍药花开时节。”“入夏以来,庭院一天美似一天,竟像个花园一般了。近日开花的又有茉莉、野茉莉、美人蕉。后院的一株苹果树也开出了白色的花。尤为可人的是茉莉,使早晨的空气弥漫着一派清香。”“绿了一春一夏的庭院,将要在秋风中渐向萧索了。眼下可人的是垂满果实的柿子树。”
扬之水对家里庭院景色的四季描述,很是吸引了大家的好奇心。有次抵京,终于如愿受邀来到长安街后边、社科院文学所旁这处著名的所在。这是北京东总布胡同一处有上百年历史的德国小洋楼,两扇朱红大门,镶着虎头铜扣,威风凛凛。开门的是扬之水,身后是“家长”志仁兄。他俩迎着我们进了院子,那是夏末初秋的季节,满园深绿。嚯,院子足足有一二千平方米,灰瓦砖铺设的小径约有一米见宽,一路向前,小路旁种着低矮的灌木,灌木往外蔓延着土坡,高低起伏,坡上自由长着各式乔木,有的新株细嫩仅一人高低,有的枝繁叶茂已蔓过二楼楼顶。假山石园内随意堆放,丛丛绿竹掩映。很多植物我叫不出名字,只依稀记得有文竹、紫藤、扶桑、仙人掌,还有扬之水写过的美人蕉、芍药。爬墙虎则布满了外墙楼壁。扬之水领着我们上了一个土坡,指着说,这是苹果,那一棵是柿子,那是……小楼之后,还有一溜平房,她说,那是厨房,也是杂物间。围墙外小院左边,云,某某某家,右边,又是谁谁谁家。那么,这个小楼的主人又曾是谁呢?答,爷爷的。噢,是她儿子小航的爷爷,也就是志仁兄的父亲。
这一小楼,上下两层,现楼下是另外一家人。楼梯已老旧发出声响,上到二楼,楼道及四壁,抬眼全是书架和书。人一走,木地板咔咔声响。是楼岁数太大了?还是书分量太重了?扬之水笑笑说,均有。入一房内,五六十平方米,窗朝后院,敞亮明媚。迎面一张高台,上边摆放着爷爷的遗像,台上供着鲜果和点心。“家长”说,爷爷走后,常年就这么摆着。房间靠墙一溜书柜,有玻璃门关闭。里边除了书,还有会议照片、亲人合影及外出游玩的照片。墙上挂着条幅,写着“澹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还有一幅镶在镜框里的贝雕砌成的工艺品。四五张沙发,都盖着白底蓝图大毛巾,便于换洗。地上铺着地毯,桌面光亮可鉴,总体感觉整齐有序。
想起一个细节,扬之水《读书十年》中曾写道:“3月18日,又购置一对‘两接头’书柜。屋里实在是塞不下了。我一边整理书,一边与前来‘参观’的爷爷说道,我的理想是能有一间书房。爷爷说,你的理想现在就可以实现嘛。把这间看电视的屋子辟给你们半间。3月19日,晚间腾挪书柜,布置书房,一直折腾到午夜。3月20日,清晨起来继续整理。总算初具规模。‘如一斋’真的是一书斋了。”这是1987年的事儿,当时爷爷健在,扬之水才33岁。
扬之水爱书,“家长”也是同谋。没有“家长”的袒护和纵容,估计这书就爱得艰难。毕竟除了书,生活还有吃喝拉撒睡。但他们愣把生活过得好像只有书,而且还相当有滋有味。《读书十年》里,扬之水流水账般地记录了每次买书的书名和数量。很多时候,都提到“志仁一道”,或是“搭志仁的车”,有一次更可爱,说:“在文物出版社购得《明式家具珍赏》(120元),为购这一册书,与志仁不知磨过多少次嘴皮子。”这该是1987年的事,当时的120元的确是大数目。磨破嘴皮子,最后得逞。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普通人家还不富裕的时候,“家长”志仁不但陪着扬之水买了很多书,还买了很多影碟和音乐碟,看了很多电影,日子过得浪漫又温馨。扬之水很详细地记录着:“5月10日,在北兵马司礼堂看美国影片《斯巴达克思》。6月24日,往首都影院看美国立体声片《茶花女》。8月18日,在电影资料馆看法国影片《梅亚林》……”再看,“1989年2月4日,下午与志仁相约在音像商店见面,购得唱片若干。2月5日,与志仁一起在王府井外文书店购得唱片若干。3月18日,志仁陪我往协和医院,后往灯市口唱片商店购唱片若干……”志仁兄就职某经贸单位,经常出差谈判,1987年有次从香港回,为扬之水订购了一台彩电,一台音响,又给她买了三套半衣裙和六套邮票。“本来还买了一盒香港点心的,遗憾的是在换汽车时丢失了。”
志仁兄俨然是家中的经济支柱和主心骨。难怪他一出差,儿子小航就嘟囔“爸爸不在,我觉得咱们两个过日子真没意思”。扬之水也不习惯,她承认“志仁出差,我的生活水平立刻下降。首先,将早餐免去,中午以面条充饥。幸而他出门之前为我买了十数包蜂蜜花生,便足可当晚餐了。(1987年4月7日)”有一次志仁出差后,扬之水就病倒了。而他一回来,扬之水病就好了。志仁说:“是我把你惯坏啦。”的确,志仁兄没出差,扬之水真是有靠山了——小航生病了,志仁会带去医院;自己要去见作者,志仁可一同前往;外地有朋友来,志仁请吃饭买单……难怪扬之水心服口服地喊他“家长”。
这一喊,就是几十年。
那天,在他们家。我们说,难得在赵老师家,赶紧求签名留念。扬之水含蓄着,催半天,才施施然到隔壁房取来一支笔,戴上老花眼镜,一笔一划写上名字,字小如蝇,苍劲有力。在我认识的名家的字中,有两人颇喜欢——北的是扬之水,南的是陆灏。这两人的字颇相似,都小而拙而雅。他俩又是老友加好友,共同走南闯北联络了很多文化老人。两人合著《梵澄先生》,大侠先请扬之水签了名,后又寄到上海,让陆灏签名。坊间还传一种说法:扬之水虽不善言辞,但写就一手明清闺秀小楷的她,凡是去信约稿的,作者从无拒绝。很多未曾谋面的文人就因她的小楷结缘。2012年董桥写《喜得扬之水小手卷》,夸道:“1996年5月我寄《英华沉浮录》初集给扬之水,她在天一阁一张花笺上写了六行小楷回我……扬之水苦读博读通读,难得书艺精湛,随手一纸蝇头便笺都见才情,都很漂亮,奇女子也……我爱扬之水书法,爱的从来是她的书不是她的法。扬之水的字我远远一看就认得出是扬之水的字。”
喝完茶,“家长”领着我们,往长安街对面一家海鲜酒店,他说我们来自广东,得吃粤菜。那一桌,竟点了虾鱼等时鲜菜。从点菜、与服务员张罗到最后掏腰包,全是“家长”的活,扬之水只顾和我们一起,美美地吃了一顿。饭桌上,不禁问,平时在家,谁买菜做饭呢?这下两人对望一笑。还是“家长”勇敢,率先说,“嘿嘿,吃食堂。社科院的食堂就在隔壁,我们只有她一张饭卡,每次都是她去打了饭回来,我沾光,一起吃。”我们愕然,又问,那小航呢?难道他下班也一起吃食堂?“对。食堂的饭很好。有时错过时间,只得自己下点面条,那就清汤寡水。”他俩很满足,没觉得吃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儿。怪不得看着小楼下那排平房,窗门紧闭,估计平时甚少开伙,厨房于他们真是名不副实。
但奇就奇在这,2005年扬之水应邀赴深圳读书月首场论坛,讲的竟是古人饮食。演讲中,她结合古诗文、绘画、实物,介绍了先秦两汉的美食、两宋的茶以及宋人生活闲趣之一的焚香。那天我在后座,听得入迷。想象现实生活中的她,该是如何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听风、饮酒、观瀑、采菊,就像她著作《终朝采蓝》中古代士人一般风雅地生活着。然而,你很难接受,她竟然每天端着铁饭盒,风风火火地穿过胡同,到单位食堂,排着队打了饭,回家与“家长”一起狼吞虎咽吧?当然,那些代表雅生活的茶角、香筒、手炉、熏笼、折扇、纸帐、镂雕古钱纹象牙管紫毫笔,你既能在她的书中看到,偶尔,也能在她书房里看到。
那天在扬之水家,除了“家长”和她,没看到其他人。我忘了问,偌大的庭院和小楼,每天谁打扫?反正不会是扬之水。记得她某天日记中写过,有次下决心打扫房间的一扇玻璃窗,上边有厚厚的灰尘,足足有十多年没有打扫过。她的时间都用于书里书外的世界,灰尘,除非列为名物考证对象,否则定不入法眼,或终究熟视无睹。
2012年秋天,扬之水应邀到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讲座,会后,读者排队签名,场面拥挤。“家长”笃立其身边,熟练地为每本书掀着书页,以便她下笔写字。两人配合默契,心领神会。同是2012年,我们在北京,世纪文景施总一行宴请,天冷,扬之水戴了一顶“耐克”小绒帽,冒着寒气进来,帅气极了。我连夸好看。她颇有些得意地说,“家长”买的,一人一顶。
看《读书十年》,1989年3月20日那一则,可能那段时间扬之水身体不大舒服,总赴医院检查,在结果没出来之前,她也胡思乱想了一下:“早晨与志仁一起将爸爸送至车站。到协和医院验血。回到家中,忽然发现庭院中的桃花不知什么时候悄然开放了?迎春也含苞欲放。又是一个春天了么?我想到了死——也许化验结果是生了癌呢,那就生日无多了吧。死倒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可以彻底解脱了。该留下遗嘱:将尸体捐献医院。对志仁说,找个爱书的女子,以免辜负了这些年的辛勤积累。如果可能的话,将我曾经写下的发表了的文字,自费印行,成一小册,算是留给小航的纪念。”日记写得悲切,也反映她的真性情。
好在,老天总是眷顾良善之人,把她留了下来,交给至亲至爱的“家长”。
(摘自《书人·书事》,海天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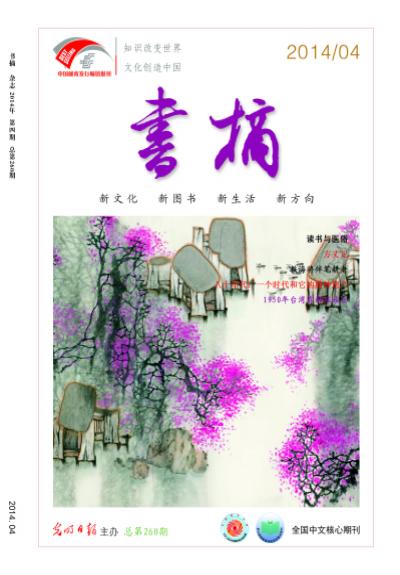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