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最鼓励并推崇的,是学习儒家积极入世的脚踏实地作风,先做好一个人,把社会建立好,才是第一重要。
大学的课程
南老师在辅仁大学上课的时候,哲学系有一个二年级学生古国治,本来要转到台湾大学的,因为得知南老师应聘要在辅仁大学哲学系开课,他就不转学了。每当老师下了课,他就替老师提着皮包,送老师上车,后来索性陪老师回台北(辅仁大学在台北近郊十几公里处),在老师家中吃晚饭。他平常没有课时,也来协会帮忙。
古国治就这样,一直到他大学毕业,按照规定去当了两年的兵,回来后,仍来帮忙。
但是他提皮包往来辅仁大学的教室,并没有那么久,因为第二年南老师就因事不教了,改请孙毓芹先生代课。
老师不去教课,这其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原来辅仁大学有交通车,每日往来台北与学校之间,南老师本来是搭乘校车来回台北的。校车上乘坐的,都是教授们,大家喜欢谈话,尤其喜欢向南老师问些问题。大家的一片热情,南老师也要热情相对,刚上课说了几个钟头的话,上了交通车还要说话,不免太累人了。
后来南老师不再搭交通车,下课后改搭计程车,再带着提皮包的古国治,先去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如此一来,教授的薪水也就花光了。
再有一个原因,使得南老师决心要辞掉大学的教职。因为台湾的大学上课很自由,所以有个怪现象,学生喜欢逃课,虽选了这门课,却常常不来上。对有些不善言辞的老师,会造成课堂没有学生的窘境。
当南老师在辅大开课时,我认得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南老师上课时虽也是选修课,教室却坐得满满的,窗外也有人站在那里听。但有些教授上课,事先同学还要到校园中拉几个同学来听讲,凑上五六个人,否则教授就太难堪了。
像这样的强烈对比,南老师早已知道不妙,为避免造成别人的不愉快和难过,自己应该急流勇退,以免他日遭忌,反而不妥。
听到老师辞去教职,我觉得很奇怪,于是南老师才把他的看法说出来。
说到辅大,使我又想到另一所大学。我有一个远亲张平堂,是师范大学体育系的教授。他虽是体育系的,但他自己喜欢读哲学书籍,自小也在家中读过四书五经之类。《人文世界》出版后,他看了几本,刚好师大有其他教授,也向他介绍南老师的文章。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曾向师大文哲方面的教授提起,为何师大不聘请南先生来教课呢?
那个教授说:如果请南先生来教孔孟学说,当然是一流的教授;如果讲道家的学术,南先生也很精通;如果是讲禅宗,那更是他的老本行;所以说,请了他来,我们这些老师怎么办呀?
这像是一个笑话,但是南老师恐怕早已心知肚明,所以只接受研究所的约聘,指导几个博士生比较不会有这类问题。更何况,博士生可以前来就教,更为简单。
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才深感创立东西精华协会的必要。这样可以针对需要而开设课程,不但大学的学生可以来听,其他各阶层的社会人士也都可以来听讲。
在协会所开课程中,如参同契、禅学、易经、中医医理等,是属于院校较少开设的课程,所以,开课后,听众永远挤得满满的,每人要缴场地费200元,经济困难的就免缴了。
南老师停授辅大的课后,许多同学就跑到四楼来听课了。
五十五岁感怀
每日忙碌不歇的南老师,一定会把周末空出来,陪着妻儿度过,或随师母的兴致,陪伴外出。老师对师母的关怀,大家都有目共睹。
多年来,虽然居家常常搬迁,但都照老师的原则,在“四大”之间。
“四大”皆空,本是佛典上的名词,地火水风就是四大。老师找居处所说的“四大”,是指四个大学,就是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政治大学、淡江大学。
他早年所住蓬莱新村,靠近台湾大学。青田街时代,则靠近师范大学。莲云禅苑时期,老师住在永康街一个巷内,靠近淡江大学及政大分部。
老师住家与东西精华协会距离甚近,步行仅十分钟的路途,节省不少时间。老师从来没有自己的房子,一方面没有经济能力;另一方面,有能力也会用在文化方面。
师母在癸丑年(1973年)到美国去探望孩子,这年南老师是55岁,头发也开始花白了。理发师劝他染发,他没有接受,还作了一首玩笑的诗:
理发师劝染发戏作
世人多畏发初白
却喜头颅白似银
免去风流无罪过
何须装扮费精神
渐除烦恼三千丈
接近仙灵一性真
对镜莞尔还自笑
依然故我我非新
虽然世人都怕头发变白,有人却觉得满头白发可与风流绝缘,少些罪过。不管白发黑发,我还是我!
尽管诗意轻松,但岁月催人也是不争的事实。
有一天,我先到三楼找到行廉姐,二人一同到四楼老师办公室去。老师说: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自己从梦中哭醒了。
老师从梦中哭醒!这真是天大的事!
原来老师在梦中又愁又急,为什么接棒的人还不来啊?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急得哭了起来。
正在此时,听见袁太老师(焕仙)喊他:“怀瑾呀!你看!那不是来了吗?”
老师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海边,回头望去,看见一个妈妈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远远地向自己走来。
天啊!还是一个孩子啊,还要等许多年啊!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老师平日一定在着急接棒的人,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
对于这桩事,我心中颇为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有接棒人呢?”
老师是临济宗的,他说:“按照临济宗的传承,是应该有人接棒才对。”
夜阑人静,午夜梦回,愁上加愁,老师想起了故乡家园,已远离廿多年了……
思乡
故园西望泪潸然
海似深情愁似烟
最是梦回思往事
老来多半忆童年
想起了故乡父母家园,不觉也想起了故乡的妻子,那原本是姨表姐的人,与自己自幼青梅竹马。局势如此,想到她艰难的处境,头发也早已白了罢!再想到童年两小无猜的往事……
忆内
辛苦艰危发早华
童年犹忆住他家
庭园百卉先春艳
蜨蝶双飞争扑花
一流人才何处去
南老师从不鼓励任何人学佛学禅,当然更反对迷信。
听起来有些奇怪,南老师不是常常在讲佛经吗?不是常常都在主持禅七修证吗?为什么说他不鼓励呢?
经过多年的观察,及南老师讲课所透露的讯息,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
南老师常说,唐宋时代,一流人才都去学佛学禅宗了;现在的时代呢,他半开玩笑地说:第一流的人才做生意。第二流的人才研究科学。第三流的人才搞政治。第四流的人才从事文化。第五流的人才去学中华文化。学中华文化也不成,才学佛。
当然,这是很痛心的话。他也常说,只有两种人可能学佛成功,一种是大智慧的人,另一种是下愚而诚敬的人。
有智慧的人能了解掌握佛法的最高意境,以及在宇宙人生中的关键点。而下愚诚敬的人不会三心二意,且能信解受持,坚定不移,而终至成功。
至于一般的人们,说他们没大智慧吧,也聪明伶俐,得失利益计算得很精,三天没有进步、没有所获,就觉上当,又要改弦易辙,就这样摇摆不定地浮沉着,度过了一生。
1976年春末,有一个从美国来访的天文博士,指名要跟南老师学禅宗。南老师初次见面,听他叙述了一些经历,他已在美西日本禅堂学了一些时间了。说完之后,南老师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学禅宗只是找一个栖身之所,大概找不到工作,心中苦闷,就躲到禅门里头了……”
刚说到这里,只见他眼泪流下来了。南老师的话虽然太尖锐一些,可能是禅宗的棒喝法门,把他的起心动念、内心深处的弱点打出来,认清事实,不必自欺欺人。
博士到底是有些学养的人,很坦白地承认了这个事实。南老师劝他努力奋斗,工作可以退而求其次,不必坚持博士的标准待遇。因为美国的工作待遇是以学位分等级的,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公司情愿雇用学位较低的人。朱文光博士在不景气的年头,不出示博士学位,只拿出学士头衔,照样找到工作。这位天文博士后来也就重回社会去工作了。
台湾许多大学都有佛学社,爱好学佛的同学们自己结社共同研究。有些社团也邀请南老师前去讲演。
南老师平时就常说,最看不惯有些佛学社的学生,见人就双手合十,平时动辄垂眉闭目,满口佛话,一脸佛相,全身佛气,没有一个天机活泼的青年样子。学佛首先要学做人,不可装出个惹人讨厌的模样。
如果有人说要学佛,学禅宗,南老师必定说:“你学这个干什么呢?这是拿一生做实验的事,划不来,还是做个平常的人吧!”或者会说:“真正想要学佛,第一步先把人做好,人格好了,才能谈学佛……”
由此可见,南老师讲经说法只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那个时代,社会上宗教文化正确见解不多,他不能不起而树立正确知见,绝不是喜欢宣传任何宗教。
南老师也时常说,他很同情出家人,出家人为了要学佛,要了生死,才舍弃了父母家庭,剃度出家。但由于种种原因,受环境的限制,出家后反而无法学习,只是过着出家的生活而已。所以他说很同情他们的处境。现在形势使然,为这些努力的出家人上课,也是一桩好因缘。
这使我想到一件事,与此类似,从前常开车外出郊游,有一个美国朋友,只要他参加,必定抢着开车。我以为他喜欢驾驶,岂知他说:“最不喜欢开车,抢着开车是因为不放心别人的驾驶罢了。”
许多人的做法,不是喜不喜欢,而是出于自己的责任感问题。
另一个老师讲经说法的原因是:如果座中有个大智慧的人,在认真修学,希望不辜负了他。
最重要的一个促使南老师常讲禅宗的原因是:禅宗这一门,一般学者涉入较少,为使其不断层故,不能不加重视。
其实,南老师最鼓励并推崇的,是学习儒家积极入世的脚踏实地作风,先做好一个人,把社会建立好,才是第一重要。如果一个社会多数人去学仙学道,就是亡国崩溃的开始,史有明鉴,不可不慎。这也是他苦口婆心多年来一贯的教化路线。
(摘自《禅门内外——南怀瑾先生侧记》,东方出版社2013年7月版,定价:34.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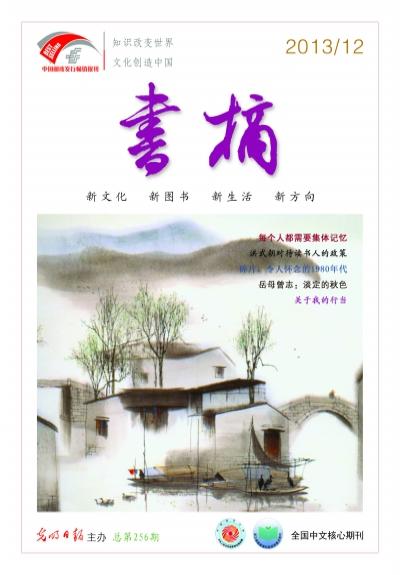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