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时期读过《西游记》,以为印度太遥远啦,恒河就是天上的银河。玄奘取经穿越大漠,大约一粒沙子就是一步路吧,如果将他碰过的沙粒每一颗都想象为星星的话,可以重建一个宇宙。印度是去不到的,那是一个神话。所以当我登上昆明飞往加尔各答的飞机时,有做梦的感觉,仿佛正在奔赴刑场,我要去的是天堂。
这是2010年3月28日,我在夜里2点来到了印度,落地于加尔各答。
导游来了,一个中年男子,黝黑、热情、神情质朴,会说简单的英语。往我脖子上套了一串白色的鲜花,香气浓烈,在这花香扑鼻而来的瞬间,忽然想起四十年前,我在昆明秘密阅读泰戈尔,他的诗,就像一个语词组成的花园。
黎明,印度的风吹着。印度这个词总是给我阴天的感觉。天亮时拉开窗帘,外面正是阴天。窗外是一个发黑的大阳台,因为下面是旅馆的大堂。夜里下了一场雨,阳台上积了一滩水,倒影映出阳台边保龄球状的陶栏杆。一只乌鸦绷着腿落下来,干练敏捷,背上斜插着两只匕首似的翅膀,印度有很多乌鸦。有个高个子的人骑着自行车在下面的庭院里驶过。另外两个长衫飘飘的男子站在花台旁说话。接着又来了一位穿长裙的女子,风在后面跟着她,把她的莎丽贴着臀部往前推着,仿佛就要飘起来。白色和蓝色的旗幡在旅馆上空招展。远处是平原,在那儿,大地依旧是主导性的力量,草木葱茏,包围着人的屋宇。那些岛屿般露出的屋宇都不高,一两层楼。一份当天的报纸已经从门缝里捅进来,躺在地毯上。瞥了一眼,头版是整幅的广告,大约是推销西装,一个系领带的男子笔挺地站在报纸中央。这场景很像一幕费里尼电影的开场。
大巴车来接我们去加尔各答市区,负责我们这趟旅行的有三个人,司机、导游和一个小矮人。行车途中,香烟一直在飘,为了使香枝不倒,还做了一个固定香炉的小装置。这汽车最神圣尊贵的位置就是这里,整部车也没有它重要。这个小神龛使我们的车子仿佛是一座移动的寺院。
当汽车驶进公路时,我看见了印度。这是之后我一直都看见的印度,我们的宾馆其实只是印度的一个相当有限的局部。广大的、普遍的印度是在公路的两旁。这一眼所见的印度令我难忘,一个旧世界。陈旧、破烂但是安详的村庄,五颜六色的垃圾、有人在旁边汲水的古井、古老的牛只、古老的田野、一列古老的火车穿过的古老大地,车厢门挂满了古旧的人们,他们仿佛刚刚从田野上收工回家。
收费站是一处监狱般的建筑,铁栅隔着,污迹斑斑。看不见收费员,一只手从铁栅栏后面伸出来接过卢比。卢比也是脏兮兮的,失去了硬度,像一块千万人用过的手帕。在印度很难看见新票子,大多数纸币都是脏兮兮的,纸币上印着15种语言。据说印度有1652种语言,18种官方语言。过了这个收费站,就进入了加尔各答。城市普遍低矮,可以看见落日和新月。河流两岸零零星星的有几栋高楼。极少装饰,平庸而实用。印度的建筑物很少象征性,看上去政府的政绩大约也不体现在建筑物上。许多大楼停工了,热火朝天的是旧日子,现代化在此地还没有高歌猛进。
一条宽阔的大河穿过城市,河岸被水泥砌成了斜坡。是那条河,恒河!恒河?我吃了一惊,恒河的支流——胡格利河。我想起在纪录片和图片中看见的恒河,无数信徒在光辉灿烂的早晨顶礼膜拜,疯狂地往自己身上灌水。那不是河流,那是一座液体的圣殿。我一直想象着朝圣之旅,想象自己如何在黑夜将去,黎明方升的时候走向那金字塔般的圣水。哦,恒河不只一处,它长达2510公里。
河岸的一处有个小庙,庙外面停着一群纸、泥巴、竹篾扎的神像,不是妙相庄严、正襟危坐的神,而是浓妆艳抹,五彩缤纷,很花哨,中间一位女神骑着马。欢乐活泼浪漫性感的神。旁边聚集着一群人,站着的、躺着的、睡着的、坐着的,孩子们沿着河岸的斜坡冲下去,一次次扎进河中。有块地空着,我走去那里站着,立即被睡在地上的印度人呵斥,这是一块圣地,穿着鞋子是禁止踏入的,我根本看不出丝毫神秘之处,也许神曾经在此站过几秒钟,只有他们知道。他们在等着时辰,一到,就抬着神像下,随河去沐浴。恒河,平庸得令人绝望,就像从我家乡穿过的盘龙江,那被改造过的水库式的河。恒河水很浑,有些肮脏的机动船在河中央突突驶过,载着用帆布盖着的物资。
从郊外向市区去,不是涌向世界大都市通常的珠光宝气的崭新购物中心,而是向着旧世界的心脏而去。各式各样的房子高低错落,丑陋、华丽、贫寒、呆板、肮脏、富态轻薄的、高贵老迈的、五光十色的、摇摇欲坠的……各色各样的什物像是刚刚从某辆看不见的大卡车上倾倒出来,散布在各处,布匹、塑料、车辆、垃圾、果蔬……晾着的、挂着的、铺着的、滚着的……令人眼花缭乱。眼花缭乱一般是相对新生事物而言,这里的丰富却是属于旧世界的眼花缭乱、旧日子的五彩缤纷、旧家什的雨后春笋。一切都被用旧了,像是二手货仓库,但没有死去,没有自卑感,继续活着、用着,用得生龙活虎、熙熙攘攘、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前呼后拥、此起彼伏。旧是伟大的,生活的目的是做旧。焕然一新在这里非常刺眼,那只会意味着出事了,反常了。堆积在历史中的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大楼,凝固的航空母舰,笨重、爬满苔藓、就像沉睡的象群。堆积在垃圾堆旁,横空出世的长方盒子式新楼。堆积如山的棚户区、市场、巷道、私家建筑……每一栋房子,无论那是豪宅还是贫民窟,一旦盖起来了,就矗立着直到死去。因此有无数老态龙钟,垂垂将死的建筑物。甚至已经死了,已经是一片废墟,那也是有主的废墟,由它废着,任何人不能擅动。加尔各答老城令我震撼。一切正在被创造出来的和已经死去的都摆在那里,像是某种天堂和地狱的混合物,古老、陈旧、累叠、堆积,涣漫,阻塞、发霉……就像岩层。与印度比起来,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历史,就太像一场大扫除了,一个忙着搬新家的国家。印度没有焕然一新,印度灰暗而深厚,那显而易见的历史感沉重得令人窒息。这使得人们的表情呈现出某种尊严,某种自我意识,自信、安详、平静。不知道为什么别的民族会那样的自卑自残自我否定自我毁灭,那么热恋归零。
大街上时常有男人在洗澡,只穿了短裤,脊背水淋淋地闪着光,哗哗地浇着水。街道边每隔一段就有一组水龙头,供路人饮用沐浴。许多人赤裸着上身干活。印度是身体很活跃的社会,随时可以感觉到身体的存在。身体只有一块很薄的布与世界隔着,这一隔反而使身体更强烈。城市里飘扬着各种各样的布,旗、衣物、帘子,到处可看见洗干净的布晾晒着,市场上到处是布,男人穿着长衫飘过,女人穿着莎丽飘过,还有裹着布的游戏队伍和尸体幡然而过,街道仿佛是就要飞起来的布匹。五颜六色,来自各种各样的信仰,来自远古的图腾,来自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原始意义已经被忘记,只留下布在裹缠飘拂。
街心也是一样生动,大街具有人行道、车行道、厨房、公园、浴室、商店、娱乐场、卧室等五花八门的功能。物与人没有等级。物不贵,人也不贱。不像别的地方,人越来越贱于物了。物被顶礼膜拜,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这是一个从容自信的城市,流行世界的拜物教在这里没有市场。所谓脏乱差的东西都是物,而人在物质之上,女人裹着莎丽、男人拖着拖鞋,牵着那只叫作物的狗悠然而过。物是一种下贱便宜可以随便糟蹋折磨毫无尊严的东西。汽车飞机电视机自行车空调什么的,都是脏兮兮的。它们的本相从来没有被遮蔽起来,它们不过是工具,谁会成天把一把粪瓢或者锄头、大锤什么的擦得亮堂堂地供着?奔驰就是代步工具,脏兮兮的奔驰只说明它代步代得很卖力。我在印度的日子里,坐过许多汽车,几乎没有一个司机按过喇叭。坐在汽车上感觉到走在路上的是人,是生命,是领导、神灵。
大街上有许多摆摊卖小吃的。除了街边的小摊,几乎没有可以正襟危坐的馆子,偶尔也有,但里面完全没有享受美食的气氛,大多只是食堂水平。印度人吃得很简单,小吃为主,大街上可以看见一排排食客坐在露天的摊子前面,各人抬着一个小盘,吃点煎薄饼和豆汤,食物真可谓单薄寡陋。据说印度的素食者大约占人口一半,他们以吃素为纯洁、高贵。肉食者鄙。吃在印度太不重要了,维持身体必须就够了,印度之味不在食物上。与民以食为天不同,这是民以神为天的地方。
加尔各答就像一位自由散漫的诗人的房间,这地方也确实产生了一大批最杰出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就在这脏乱差中。生活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生龙活虎,人们忙忙碌碌,只为了一件事,生活,更激情或者更腐烂地生活。这城市总是在过节似的,而节日到来,那就是彻底疯狂了。而印度隔三差五就是节日,有无数的神要祭祀要过节。热闹混乱喧嚣,但不焦虑,这是生活本身的热闹混乱喧嚣,生活的气质。
加尔各答非同凡响,这不是世界流行的那种拜物主义的城市。活泼泼地,犹如永远水泄不通的纽约时代广场,但那是拜物者的狂欢节,巨大的电子广告吸引着无数游客像长颈鹿那样仰视着摩天大楼。“一个被我们忘却的事实是,需要管理的是物而不是人。”加尔各答却在黑暗里星星般地睁着眼睛。印度就像一场巨大的行为艺术,似乎全部表演就是要把现实的真相呈现出来,令人失去入世的信心。在印度旅行,我时常感觉到那种无所不在的超越性,你不能拘泥于现实,拘泥于现实,被沼泽吞没的是你自己。
印度依然保存着过去,一望可知。印度的过去还没有退回到史书中,印度的过去活着,这是加尔各答给我的最深刻的感受。
(摘自《印度记》,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定价:6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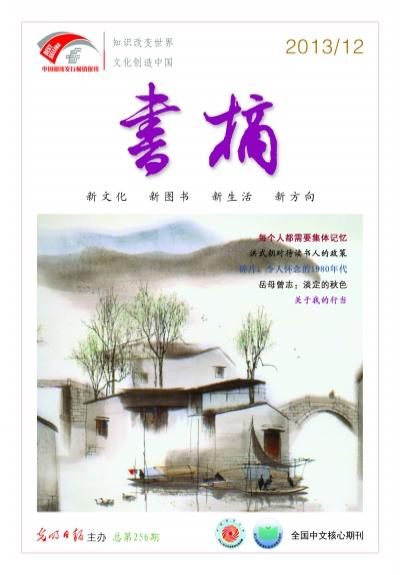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