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民国,这个充斥着强烈的情绪与变革的年代让爱情走向了生命的巅峰,更让女性的命运与选择在历史的大幕下多了几许苍凉与悲情。
也许,在我们这样的年代里,写不出伟大的爱情,然而,就如爱情是我们从来无法摆脱的魔咒,我们依然能够沉浸于那个时代,最美的文与最动人的故事;最磅礴的时代与最有魅力的女人;最悲情的爱情与执著的追求,民国时期的爱恨情仇,浓烈得像一杯醇酒!
孟小冬晚年在香港,几乎不化妆,唯一的盛装露面是有回朋友宴客,她在姚玉兰女儿的操持下,点了点粉脂,朝灯下一坐,静默端然,气场膨胀,华美清艳,恍如昨日。席间补妆,她还是用手抹了盒子里的唇膏,再涂到嘴上——依旧是二三十年前的操作方法。有人写,正是在那样的场合,如此做法,才看出孟小冬的“不入流”来。
人近黄昏,在香港,孟小冬一个人住。和梅兰芳的华丽恋情,已经是泛黄的旧篇章,与杜月笙的相濡以沫,也成了身后的故事。她一个人度日,清简自然,穿着布旗袍,平底鞋,一个发髻挽在脑后,普通的好似街边买菜的老太太。她经常与朋友们聚会,赌马,也打麻将。麻将桌上,孟小冬也开玩笑,说:“现在香港都流行大胸美女。哪天能流行平胸的,让我这样的也能再赶个时髦!”天晴的时候,她也出去走走。只是,她不再唱戏。谁要跑到她家里说戏,问:“孟老师我唱的怎么样?”孟小冬永远说好。她不愿意得罪人。
后来到台湾,孟小冬租了个房子,也还是一个人住,靠着杜月笙留下的钱和当年自己的积蓄过活。麻将还打,朋友还是招待,她还学习英文对话,刻章,打拳,不亦乐乎……唯独戏,依旧不唱。连清唱都不唱。最后一次清唱,是在香港唱给张大千听,已经是天大的面子。尽管如此,“冬皇”孟小冬的名头,在戏曲圈子却照旧响亮,仿佛一个古老又神奇的传说。
有一次,有人问孟小冬:“您还预不预备唱啊?”孟答:“胡琴呢?”曾经沧海,繁华已去,何必再唱?最后一个给她拉琴的王瑞芝,也去世了。她落得平静。
20世纪30年代,孟小冬曾说,“要嫁就嫁一个跺跺脚上海滩也要震一震的人”。之所以要如此出嫁,不是因为虚荣,而是孟小冬名气太大,想要过平常日子,也只能如此。所以,晚年的平淡生活,也正是她心向的状态。据说孟小冬晚年很爱看电视,家中常常两台电视齐鸣,她学电视中人的声调表情,惟妙惟肖。熬至滴水成珠,孟小冬无须再向谁“献艺”,自娱自乐,足以。
蔡康永在台北见过暮年的孟小冬。地点是仁爱路在地下一楼的鸿霖西餐厅。“长桌末端,坐着一位穿着灰色宽松旗袍的圆润老太太。”蔡康永写道,“当时听我爸说,孟小冬人称‘冬皇’,是当年京剧界第一坤生,我更是头晕,其实当时台北也有坤生演京剧,但那是戏台上的事,戏台上的人怎么会坐在餐厅里吃饭?我再转头看看老太太,想看出点‘冬皇’派头,但只记得望去一片影影绰绰,灰扑扑的,实在看不出‘冬皇’的架势。”
影影绰绰,灰扑扑的……人在台北,出街用餐,孟小冬还是不化妆。她不需要“架势”,也谈不上要“入流”或者“不入流”。
风流过往,红尘旧事,俱已不在。
来者不迎,去者不送,哪怕是女人最精贵的容颜。
孤傲的女子不用化妆,因为她并不需要再刻意给谁看到。
小凤仙后来
小凤仙是八大胡同的传奇。
正史里没有关于她的记载,野史里却充满了她的传说。小凤仙在八大胡同云吉班不算红牌,样子也只是普通,但因为深明大义,帮助共和名将蔡锷逃出袁世凯的软禁,而蜚声四海。小凤仙更像是男人的一个美梦。英雄陌路,美人温存,风尘里的红颜知己,给了英雄足够的勇气和力量,第二天,英雄继续上路。她太像夜奔的红拂,也仿佛自刎的虞姬。男人的战场,从来都需要女人的柔情。
1915年,蔡锷因喉疾在日本去世,小凤仙得知,悲恸欲绝,送上挽联说: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蔡锷死后,小凤仙艳名大噪,她凭借一个“美人恩+家国恨”的故事,登上了人生的顶端,硬是靠口口相传,成长为一代名妓。许多人去云吉班,点名要见小凤仙,更渴望能与小凤仙一夜风流,从心理上满足“与蔡将军同靴”的怪癖好。蔡锷的学生与部下,对小凤仙则极力排斥,怕她影响蔡锷的名声。而小凤仙却悄然转身,隐没人海,成就她与蔡锷的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情。有意思的是,蔡锷的声名,非但没有因为小凤仙的存在而跌低,反而因为这个绯红的注脚,成为后世人心中,柔情铁汉的代表。
小凤仙后来的故事,有多个版本。有人说,她离开了云吉班,四海漂泊,无从追寻。也有人说,小凤仙去上海参加了蔡锷的追悼会,哭得死去活来,而后回到北京,留下绝命书,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在火车上,她想服安眠药自杀,却被颠簸的车厢碰撒了药,没死成。到了天津以后,小凤仙辗转流离,嫁给了一个军人。战火纷飞,军人命运起伏不定,小凤仙也仿佛小舟一叶,跟着浮浮沉沉。
传解放前夕,小凤仙再嫁,对方是一个锅炉工,姓李,比她大5岁。锅炉工带着跟前妻的14岁女儿,小凤仙待她如亲生。为了讨生活,小凤仙外出做工,找到一户张姓的干部人家,去做保姆。她改了名,换了姓,叫张洗非。前尘往事,似乎也要跟着这个名字渐渐磨细模糊。
据梅兰芳秘书许姬传先生回忆,1951年,梅兰芳去朝鲜战场演出,路过沈阳,小凤仙曾给梅兰芳写信,希望能见上一面。见梅兰芳时,她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带上了女儿,当面诉说了当年的种种,和蔡锷的交往,怎样出走天津……她希望梅兰芳能帮帮忙,改善改善生活。梅兰芳义不容辞。后来,小凤仙在政府机关当上了保健员,有了稳定的工作,平平凡凡地过着日子。
卸了历史的浓妆,小凤仙素颜以对,平静,凄清。时光的大潮,冲刷了当年的华彩,她只是做回普通人。有一个丈夫,一个孩子,一份工作,买菜,做饭,为孩子的未来操心。后来女儿嫁了人,她又回归孤独。
传奇的故事,已经被说得密密匝匝,人们只是醉心于这个故事,故事里的人后来如何,似乎也不再重要。说是有一天,小凤仙在听广播,广播里正说着她和蔡锷的故事。多年埋藏心底的秘密,忽然好像海底的贝壳,因为一场旋风而被卷入海面,重见天日,小凤仙感怀往事,泪如雨下,指着戏匣子跟人说:“那里面说的就是我的事情啊!”刚说完,又猛觉自己说漏了嘴,赶紧说:“你一定要替我保密,不能对外人说啊!”
小凤仙后来过得说不上幸福,也说不上不幸。她像一颗贝壳,被海水卷出海面,现在,她只是慢慢回落下去。
要有多坚强
张爱玲跟胡兰成绝交,写了一封信: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随信附30万元,作为胡兰成的逃难经费。情至义尽,恩断义绝。过了一些年,胡兰成写《今生今世》,大谈与张爱玲的过往,得意万分,上半卷出完,张爱玲忽然给胡兰成写了一封信:
兰成: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12月27日
明为借书,实为警示。大抵意思是告诫胡,不要在下半卷再乱写。胡兰成果然没有再写。后来张爱玲给夏志清写信,谈到此事说:
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
彼此不痛快。老死不相往来。只不过张爱玲后来还是写了《小团圆》,里面谈了胡不少,死前不久还叮嘱《小团圆》不能出版(可惜还是“被出版”了)。
沈从文和丁玲是当年一起北漂的朋友,但后来也闹到决裂。
丁玲被国民党软禁的时候,沈从文开始以为她牺牲了,很激动,也很伤心,写了11万字的《记丁玲》发表。后来得知她没牺牲,就又去南京看她。但丁玲这时候与沈已经有“芥蒂”。原因是:丁玲认为自己在坐牢时,沈回湖南探亲,路过常德,没去看她的母亲;再一个就是,“哪里料到,后来沈从文却不愿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
丁玲认为他胆小,怕担责任,经不起风风雨雨,尽管嘴上说“还是原谅他”,但新中国成立后,在会上碰到,沈丁碰面,丁直接走过去。开始当沈空气了。
1979年,丁玲无意中看到沈从文的《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大怒,说沈是在写小说,她在书上做了许多批注,但没写文章反驳。后来,《诗刊》要发胡也频的几首诗,请丁玲写几句话,丁玲写了《也频与革命》,又捎带写了沈从文,大致意思是说沈从文市侩,当时不听人劝告,一心想依附胡适往上爬,还称:“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我描绘成为一个向往‘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
丁与沈彻底决裂。别人问起两人之间的事,沈只说自己记不清了,以丁玲的话为准。只是在自己的文集中,不再收录《记丁玲》和《记胡也频》。
秦德君和茅盾也绝过交。两人在日本你侬我侬,回到中国,大孝子茅盾迫于家庭压力,与秦德君协议分手。两人商定分手时限:四年。秦德君去兑现分手承诺:人工流产。分手后,茅盾失踪,秦德君经受不住分手打击,实施自杀,方法是:吞下两百粒安眠药……好在,秦德君命大,没死,后来还几次嫁人,在国统区的重庆,她还一度风光。两人在重庆相见,茅盾有些悚然。转头去香港写下《腐蚀》,滋味深长。新中国成立后,秦茅二人在不同场合见过,心里有数,但嘴上已经无话,互当空气,形同陌路。
男女之间的分手、绝交,终究逃不过一个情字。因为曾经互相伤害,所以分手后,朋友都没得做。说恨吧,也不全是,有的只是喟叹、怨念,刻意地避而不见。嗬,要有多坚强,才能念念不忘。不过话说回来,人生在世,从未与人绝交,也无趣。
(摘自《流苏与娜拉》,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版,定价: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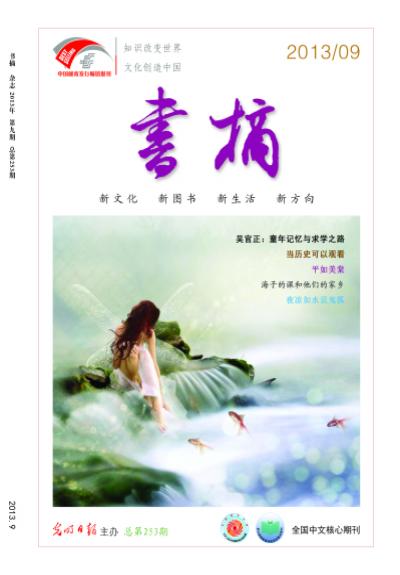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