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看过王先生张先生结婚照的人,都会被张先生的美震住,我很想听听王先生讲讲他们当年的爱情。但听来听去,王先生的个人史似乎也都是大写的,所以,面对王先生,谁都不会有八卦心态。有一回,我去美国,他让我带书给他一位美国朋友。我当时一定是有些轻浮地说了句,是女孩吗?王先生正色道,一位教授。
常常想,王先生这一代人的感情生活大概对他们自己而言,是比较次要的,所以,他留下了那么多著作,但却没有一本完整的自传。我们感到遗憾,但王先生一定认为,他是作为思想家留在历史里的。
一直以来,王先生客厅里的话题都是家国大事,他知道我写点专栏文章,常常也说,《信报》上倒一直看到你的文章。不过只有一次,他表扬了我,就是那篇《悼三峡》,他认为是有关怀的文章。而他自己,在瑞金医院的最后时光里,还在不断地发表新的思考成果。最后一次去看他,他已经不愿意进食,单靠营养液维持。我跟他说起不久前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他和林毓生先生的对话,在网上被到处转载,他就显出高兴的样子。而当时的他,就算说一个单词,也需要积聚力气。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给《文汇报》的陆灏打了个电话,询问他和林毓生先生的第二篇对话。据陆灏说,在这篇未能发表的谈话中,讲到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传承关系,几乎可以视为王先生的思想遗嘱。
这篇遗嘱还没公开,王先生已经在汶川大地震到来前离开。好像当时没特别难过,因为心理上大家都准备了很久,但是抬头看到王先生引鲁迅的话写给我们的字——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想,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还是无限黯然。
这个春天走了这么多人,天堂从人间要走了一个又一个思想者,风风雨雨中,谁能透过一个世纪的沧桑,再次鼓励我们:“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多么怀念从前,春天的下午,王先生突然来了兴致,唱起以前教会学校的校歌,英文歌曲,我听不明白,他就一句一句解释;他问我在学校上什么课,我说莎士比亚,他就非常高兴,从哈姆雷特说到李尔王,讲亨利五世讲理查三世,说完柯勒律治的观点说他自己的,让我不停遗憾他如果能开一门莎学研究会多么不同;还有许许多多的快乐时光,我们结婚,他来新房坐,坐在靠椅里,吃了一身的花生壳,然后说,我比较喜欢吃花生。然后有人小声嘀咕,最喜欢的,当然是讲话喽。
讲话,应该是王先生的最大爱好吧。病床上的他,不断地积攥力气,关心这个询问那个。他说得那么痛苦,医生明令,你们说,王先生听。他沮丧地躺下来,无助如同一个孩子,想起他最看重的尊严和自由,想起他从来没有服从过的命运,令人不得不觉得,最后的时刻来了。
五月九日晚上十点四十分,没有亲朋好友的注视,王先生一个人走了。豹子独行,这是我们开解自己的话,豹子已无言,而我们可以接着做的是,把自己的那个“人”字写好。这是他和贾植芳先生都引以为傲的事。
张中行:地下室里的张中行
第一次见张中行先生,是在北京沙滩后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地下室里。那是一九八九的冬天,记忆中北京特别的冷,冰点以下。
那时,张先生已经八十出头,每星期二换两部公交车到出版社去,帮着看点稿子。然后就在招待所住两夜,星期四一早再换两部车回北大的住处。他在《读书》上的连载已经引起读者的反响,所以推荐我去见他的朋友问我:你想见余永泽吗?见我没回过神,又说:就是张中行,不过你见他面可千万别提余永泽。
我当然是提了,谁熬得住。当时也没有人告诉我,张先生在“未名四老”或者“燕园三老”里占着席位;我不学无术,亦不知道他是国学大师,只当他是一位有学问的退休老编辑。再说了,当时年轻,年轻就有放肆的权力,所以,我竖子不可教地问上门去,《青春之歌》写的就是您吧?他淡然一笑,说,我不会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人生对世事,我会在下一部书里说清楚。下一部书正在写,叫做《顺生论》,我出了会寄给你。我并没有真的以为,他会记得把一部还没写完的书,寄给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人。所以,后来收到他自己包裹自己跑到邮局寄来的《顺生论》,我自己倒快忘了当时地下室的谈话。
现在,张先生走了,媒体说他是布衣大师,仿佛他不应该是布衣,或者他自己不应该安于做个布衣。看新闻,张先生的葬礼也称得上隆重,但是,想起好多年前,他在地下室的那种安然自得,觉得还是“老编辑”这个身份适合他。虽然他的学问后来我也深有领教,不过,他那么深的学问,却从来不唬人。
我还记得当年和他聊天,问过他一些作文技法之类的问题。张先生举自己的例子,当年顶头上司叶圣陶先生对他说:好的文章,你在这屋念,那屋的人听见了,不以为你是在念文章,而以为你在说话,这就是作文的最高境界。说完,他又是淡然一笑,我想他一定觉得自己是做到了。所以,张先生的学问和他的文章一样,谁都能看得懂,他只用明白话讲人生的道理。他的学问我这里没资格谈,记得的是他朴素的人生教导,他说,老婆有四种: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可意的不多,不可忍的就离了,大多数人介于可过与可忍之间,他自己就是。
后来在报上看到记者采访他,记者问他《顺生论》中提到的“利生”“避死”,何以为善?这与“贪生”“怕死”何异?他的回答很张中行:“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这不是什么软弱,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张先生的人生大抵也是如此,只要可忍,就可过。将近百年的风雨沧桑,任由嬉笑怒骂,他一直活在自己营造的荒江野老屋中。后来这间屋子庇护了多少天下同道,没有人知道。所以,我想他的哲学是小民的哲学,至于你要问为什么?不为什么。
但是,在这个利己主义大放光芒的时代,突然大力祭奠张中行,我总觉得有点可疑。要知道,他的小民哲学,对抗的是高调大我,而现在,G大调的青春之歌早就没人唱了,全是小小小民,祭起张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黄裳:老头儿开会
因为陈子善老师在师大,所以,常常有老头儿开会的场面。老头儿互相调侃,旧时光哗啦解冻,当年醉红颜,今朝忆青涩,哪里还有什么顾忌。老头儿说话比谁都生猛。
黄裳作品讨论会上,一向坐主席台的官人们纷纷靠边坐。这边角落是头文字“总”的总裁、总编和总管,那边靠门的是一溜“长”结尾的局长、处长和科长,今天没他们说话的份儿。因为一线坐着邵燕祥、王充闾、郑重、黄宗江、李济生、谢蔚明,年纪一个比一个大,声音一个比一个响,那话儿,也一个比一个长。
黄宗江先生开门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在座还有比我更老的老头,然后,忙不迭地抖料:当年容鼎昌跟我说,唱戏得有个艺名,于是他帮我起名“黄裳”,可我觉得这个名字太过华丽,觉得还是父亲给的名字好,就没用。没想到,容鼎昌马上将“黄裳”收作自己的笔名,一用六十年。
本来,我猜黄宗江先生的意思是想一次性终结“黄裳艳说”,可是,比他更老的老头、还有四个月就九十岁的谢蔚明先生才不管,抢过话头:“黄裳”分明是“黄宗英的衣裳”,怎么成了你黄宗江的衣裳?我们台下坐的,多是荤人,也都愿意相信那是黄裳一片冰心在笔名,再说了,钱钟书赠送的对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当事人黄裳也没反对啊。
看老先生斗嘴实乃人生乐事,嘿,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说话比我们还孩子气。可是,真要觉得那是孩子气,就错了。听听老顽童黄永玉说了什么?永玉先生人是没到,但写了文章来,一开头就说:“黄裳生于一九一九年,这是开不得玩笑的时代,意识和过日子的方式全世界都在认真地估价,‘生和死,这真是个问题!’哈姆雷特这样说;‘剥削和被剥削的’,十月革命这样说。黄裳比共产党年长两岁,他是奉陪着共产党一直活到今天的。”
听这些老头儿说话,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老头儿活灵活现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它既可以解释对甜姐儿的痴情,也可以解释他当右派时候,一声求饶都没有的苦熬。永玉先生说,“从历史角度看,哭的时间往往比笑的时间充裕”,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的黄裳先生是“大庭广众酒筵面前也几乎是个打坐的老僧”。
老僧没有来开会。他说,今天是公审我,我来做什么。公审状一箩筐,我听下来,结论有二:黄裳的散文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就像托尔斯泰称赞契诃夫文章说的“既美丽又有用”;黄裳本人是神,想想看,五十年前他不仅开过美军吉普车,居然还是坦克教练!这样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定是有一说一,不随时风飘摇,而且可以做到五十年不动摇。
说五十年不动摇,证据就是《插图的故事》。这本书的序,写于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二日。当时“编校甫定”,“罡风忽起”,书稿“从此压在箱底”。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二日,黄先生重写《千秋绝艳》作为跋语,此书才得以出版。这恐怕也是中国出版史上压箱底时间最久的一部书稿了。一放五十年而未改一字,足见其“不动摇”了。
(摘自《永远和三秒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5.00元。本文摘选自书中《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和《二十世纪感情备忘录》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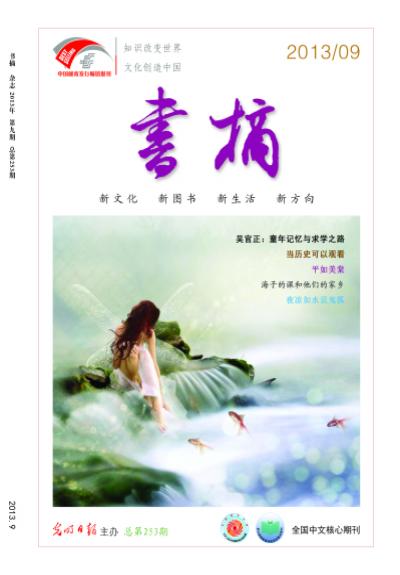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